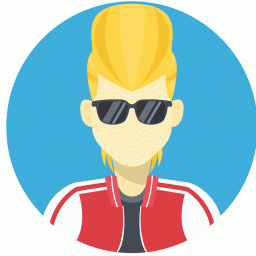陈独秀与章士钊四十年交往的恩恩怨怨
时间:2022-06-12 07:50:06
他们结识于二十世纪初,那是个风雨如晦、灾难深重的岁月。为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走到一起,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后来,他们因政治信仰的迥异而分道扬镳。陈独秀一生不能见容于主流社会,牢狱、困厄、疾病几乎伴随他生命的全过程;章士钊则大不一样,他当过国民政府的部长,成为蜚声沪上的大律师。他们的个人境遇可谓“南桔北枳”、苦乐各异。可是,每当陈独秀遇到困难时,章士钊总是不请自到,努力为老友解除困苦,竭力维护他们之间的感情和友谊。
文字知音
1902年3月,章士钊经好友汪希颜介绍,在南京与陈独秀相识。此时,年轻的陈独秀已晓有名气,有“皖城志士”之称。次年4月,沙俄侵略者占据东北不走,并向清政府提出七项新要求,企图永远霸占东北。沙俄的行径激起留日中国学生的义愤,他们发起拒俄运动,组织义勇军,准备与沙俄在东北血战。
刚刚由日本回国的陈独秀立即在安庆积极响应。5月17日下午,安庆藏书楼内集结着来自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和桐城怀宁公学的二百多名学生。这天,气候窒闷,大雨倾盆。陈独秀首先登台,手中拿着一叠纸,侃侃道来。会场内静寂肃然,人们义愤填膺,更有人低头捂脸,唏嘘呜咽。陈独秀加重语气说道:“我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即知解而亦淡然视之,不思起而救之。”对国人的麻木心理,陈独秀痛心至极,他大声疾呼:“我等既稍育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人岂非无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国虽居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会后,他还倡议成立安徽爱国学社,以“联络东南各省志士,创一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侵凌”。陈独秀的演说震动了清廷,夜色茫茫之中,陈独秀不得不乘一叶小舟离开安庆。
当陈独秀在安庆藏书楼慷慨陈词时,时任《苏报》主笔的章士钊已将陈独秀的演说词和《安徽爱国会章程》在《苏报》全文刊载,立刻在上海乃至全国产生巨大的舆论影响。不久,《苏报》因宣传反清革命,被公共租界工部局查封,这便是震惊全国的文字狱――《苏报》案。
陈独秀来上海投奔章士钊时,《苏报》案已近尾声。两人相见,分外高兴。章士钊从报架上抽出一份《苏报》说:“仲甫,你人在安庆,可是你的演说却已风传上海了。”陈独秀读完《苏报》刊载的演说词,面露感激之情,微笑着说:“行严,我可是动嘴,说说而已。你可是动笔,煽动人心了。”两人相视而笑。“仲甫,我正在筹办《国民日日报》,以继续《苏报》未竟之事业。”章士钊端起茶壶,给陈独秀斟满一杯水,又继续说道:“你来了,也使我办报的信心更足了。不知仲甫兄意下如何?”“再好不过了,行严,只要是鼓吹反清革命,我陈仲甫决无二意。”陈独秀欣然应允道。
《国民日日报》终于创刊了。它依然宣传反清革命,并且在《苏报》的基础上,栏目设置有了大的改动和创新,文章内容多是揭露昏庸腐败的政治和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所以,发刊未久就风行全国,被称作《苏报》第二。二十多年后,章士钊在忆及这段往事时,还兴趣盎然地写道,陈独秀“东游不得意,返于沪,与愚及沧州张溥泉、南康谢继石共立《国民日日报》。吾两人蛰居昌寿里之僻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亦不浣。一日晨起,愚见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计。愚骇然曰:‘仲甫,是何物耶?’独秀徐徐自视,平然答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
《国民日日报》深受人民欢迎,必然招致反动势力的忌恨。上海知县布告不准市民购买《国民日日报》,沿江省抚又查禁《国民日日报》,并不准邮局代寄。12月初,《国民日日报》被迫停刊,陈独秀在上海无事可做,只得与老友话别,秘密返回安庆。
1904年初,陈独秀风尘仆仆来到芜湖,与房秩五、吴守一等筹办《安徽俗话报》,凡事都已就绪,却找不到可靠的地方印刷,同仁都为此事犯愁。这时,陈独秀想起章士钊的上海大陆印刷局,便立即写信求援,章士钊很快回信表示支持。于是,《安徽俗话报》自创刊起,几乎每期的稿件都由陈独秀统审后,寄往上海大陆印刷局,印好后又寄来芜湖。恰逢此时,章士钊和杨笃生在上海成立爱国协会,进行反清革命。章士钊自然想起陈独秀,去函芜湖让其速来上海。陈独秀来到上海后,便由章士钊介绍加入爱国协会。此时,革命党人正在策划暗杀清廷大员,他们积极参与这一活动。
同心爱国
1914年5月,章士钊从日本来信,说他已取消欧洲之行,现在日本办《甲寅》月刊。此时,陈独秀因遭袁世凯亲信、皖督倪嗣冲的通缉而逃到上海。二次革命失败后,反袁斗争走入低谷,陈独秀也暂时静下心来,躲在亚东图书馆著起书来,他的《英文教科书》和《字义类例》,便是这时完成的。可是这两本书销路不好,当然也就难以维持生计。接到老友来信,陈独秀百感交集,立即给章士钊复信说:“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绝断,不独党人为然也。”他毫不隐瞒自己的生活窘况:“仆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章士钊接信后,便将它在《甲寅》上发表,并附上按语说:“了了数语,实足写尽今日社会状态。足下无意书之,故愚宁负不守秘密之罪,而妄以示吾读者。呜呼!使今有贾生而能哭,郑侠而能绘,不审所作较足下为何如!”章士钊还一再邀请老友速来日本,共同编辑《甲寅》。很快,陈独秀便由上海来到东京。还是在上海时,章士钊便将所著《双秤记》,交苏曼殊带给他,务请为之作叙。陈独秀到日本后才完成这篇叙。他在叙中说:“作者称此书为不祥之书,予云亦然。今以予不祥之人,叙此不祥之书,献于不祥之社会。书中人不祥之痛苦,予可痛哭而道之。”陈独秀明确表示同意书中的观点,那就是国家应“主张人民之自由权利”,国家的存在应该“维持及发达个体(人民)权利耳。个体权利不存在”,国家“遂无存在之必要”。他还在叙中悼念亡故的革命战友赵声、杨笃生、吴越、陈天华、何梅士等,大力张扬他们“有道德、有诚意、有牺牲精神”。
章士钊读完这篇叙后,十分满意,只是觉得似有未尽之言。他对陈独秀说:“仲甫兄,你的这篇叙,谈国家和个体权利的关系,很有见地。如果能循此做篇文章,岂不更好?”陈独秀也早有此意,说:“是啊,国人对此中道理,往往不甚了了,我早就想做篇象样的文章。”
“噢”,章士钊似乎想起了什么,指着“叙”上的署名说:“仲甫,你怎么又叫起‘独秀山民’了?”
“怎么,只允你在烂柯山做仙人,就不许我回独秀山作一介草民?”陈独秀讪笑着,敲点着《双秤记》封面上的笔名,反唇相讥。
“独秀山民”章士钊念叨着,突然惊喜地说:“想起来了,你的家乡有座山就叫独秀山,噢,好、好!”
陈独秀不分昼夜地做这篇“象样的文章”,也不知熬了多少个通宵,这篇文章终于做出来了,题目就叫《爱国心和自觉心》。这一年的11月10日,《甲寅》第1卷第4号将署名“独秀”的《爱国心和自觉心》和署名“独秀山民”的《双秤记・叙》同时发表。这篇文章观点新颖、文笔洗练,直面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思想,提出全新的国家观念。文章写道:“范围天下人心者,情与智二者而已。所谓‘情’即是感情,‘智’即是智识。”陈独秀认为自古以来,中国人要么全凭感情用事,如屈原满腔热情,“愤世忧国,至于自沉”;要么智识超凡脱俗,如老子虚谷无为,“了达世谛,骑牛而逝”。这两种极端都是不足取的,可是令人惊骇的是,“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既缺爱国人,又乏自觉心。“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他说,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不正确的,往往把皇帝同国家混同,把爱国与忠君相等。自古以来的统治者根本就不是为民谋利的“建设国家者”,纵是所谓“圣君贤相”,其所作所为,也“皆以谋一姓之兴亡,非计及国民之忧乐”。这样的国家,“实无立国之必要,更无爱国之可言”。他还写道,袁世凯窃得的中华民国,政治黑暗、法纪松驰、官吏贫污、兵匪日盛,“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所以,他得出结论:“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
章士钊理解陈独秀的良苦用心,他对陈独秀说:“你的文章功不可没,功在唤醒沉睡麻木的国人。你之所以危言耸听,正话反说,其目的是争国民的自由人格和权利。‘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这句话说的实在好。‘东方欲明星烂烂,汝南晨鸡登坛唤。’仲甫,你可是那只驱暗报晓的晨鸡啊!”辛亥革命后,陈独秀和章士钊就一同为满清、缔造共和而协力奋斗,他们这种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的情景,给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吴稚晖在《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中回忆道:“黎元洪由副总统代任大总统时代的内阁,即定于上海霞飞路章先生的宅内。陈先生却复演赤壁之战:章先生充做诸葛亮,他充做鲁肃,客散之前,客散之后,只有他徘徊屏际。”如果说倒袁以前,陈独秀是章士钊的助手,是“鲁肃”,那倒也是实情。但是倒袁以后,陈独秀张臂迎来的新文化运动,则另是一番情景,他再也不是陪衬、助手,而是主将和领袖。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后改为《新青年》),从而拉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此时,章士钊也已将《甲寅》迁到上海。说起此事,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章士钊在日本办《甲寅》时,竟和一位日本军人的夫人相爱,这位军人得知后,怒火中烧,写信给章士钊,约定时间、地点,要和章士钊比武决斗。章士钊一介书生,怎敌寒气逼人的锐利刀剑,只得与陈独秀和苏曼殊商量,他们都一致劝说章士钊快快回国,以避锋芒。这样,《甲寅》便随章士钊迁来上海。
1917年1月,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时,《新青年》随之进京。几乎与此同时,章士钊也来到北京编辑《甲寅》。章士钊充分认识到老友的影响和作用,因此他请陈独秀帮助他网罗文友,以利《甲寅》的编辑和发行。陈独秀是个热心人,一一给朋友去函,请他们既要给《新青年》投稿,又要给《甲寅》投稿,可谓不偏不倚。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甲寅》准于二月间可以出版,秋桐兄不日谅有函于足下。《青年》、《甲寅》均求足下为文。”在给“蜀中名宿”吴虞的信中,希望其将所撰稿件全部寄来,“分载《青年》、《甲寅》”。
认识分歧
1918年5月,南方桂系军阀排挤孙中山,改组广州护法军政府,岑春煊为主席总裁,章士钊被委任为秘书长。次年2月,章士钊参与上海和会的谈判。陈独秀对军阀和政客从不抱任何幻想,他认为所谓“‘南北议和’都重在党派的权利,什么裁兵废督,不过说说好听,做做面子”。他还将“上海和会”和“巴黎和会”比作“两个分脏会议”。陈独秀主张中国问题非“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显然,章士钊作为军阀的代言人和斡旋者,陈独秀已不可能与他意气相投、并行不悖了。
但是,他们对患难之中所建立起的友谊,都分外的珍惜。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章士钊知道后十分着急,急忙写信给北京政府代总理龚心湛说:“陈君英姿挺秀,学贯中西。皖省地绾南北,每产材武之士,如斯学者,诚叹难能……育一人才,至为不易,有焉忍遽而残之耶?特专函奉达,即请饬警厅速将陈君释放。钊与陈君总角旧交,同岑大学,于其人品行谊,知之甚深。敢保无他,愿为左证。”在各方的有力声援下,陈独秀仅被拘押98天,便被释放。当新思想如潮涌来时,章士钊却扮演“和事老”的角色,对此,陈独秀非常失望。在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上,章士钊鼓吹“新旧调和”论,认为今日政治腐败已远甚于前清,究其原因“其所迎者新之伪,而旧之真者则已破坏无余也。”所以,拯救中国应该是“新机不可滞,旧德亦不忘,挹彼注此,逐渐改善”。陈独秀极不满意“新旧调和”论,批评说:“新旧调和只可说是由人类惰性上自然发生的一种不幸的现象,不可说是社会进化上一种应该如此的道理。”
1921年2月,章士钊由黎元洪资助,重去欧洲游访,考察西方政治。陈独秀知道后,立即发表文章表示欢迎。他说:“前在报上见过章秋桐论‘败律’那篇文章,后来又听说他出洋读书去了,我赞成他这种态度,我并且希望政学会诸人都取秋桐这种悔惧的态度,方不是精神上永远绝对的失败。”章士钊到底“悔惧”什么呢?原来,他抛弃了所推奉的西方代议制的政治思想。章士钊从英国回来的最大收获,是完成了《农业救国论》,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农业立国,这种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陈独秀无情地批评了“农业救国”论,指出所谓“农业立国”,其后果将是拒绝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回复古代之简陋的生活和文化”,是开历史的倒车。此时,章士钊又刊登广告,集资十万元恢复《甲寅》。陈独秀讥讽道:“行严君!以十万元办一周刊就是在日本也不敢想,‘何况中国’,比较一下‘现在中国人之生活与文化更简陋的社会,’难道有此“穷奢极欲之需要可能”?后来,章士钊成了段祺瑞的亲信,担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训令共产党为犯有“内乱罪”的非法政党。陈独秀对章士钊的变化,已经觉得“令人骇怪了”!他在《向导》上,写了一封致章士钊的公开信,信中说:“老朋友,你所长的司法部如果真有这道训令,便实在令人不解了!”针对章士钊的中国是农业国,故不应该有政党的言论,他指出:“若不能绝对否认中国也有工农阶级之存在,便不能说中国不应有共产党。”他还奉劝道:“我记得先生是一个深知政本的人,是一个反对好同恶异的人,我还记得先生是曾说有志研究马克思学说的人,并且俄德共产党曾传说旅欧中国人中有一个倾向共产主义的章行严先生,所以我还不象一般人那样轻蔑先生,希望先生对于我以上的陈述有一个公开的答复。”
1925年7月,在段祺瑞的资助下,《甲寅》再次复刊。章士钊纠合一班旧文人,以此为诋毁新思想的阵地,公开提倡旧礼教和旧文化,形成了一个复古的“甲寅”派。鲁迅对此认识得很深刻,他说,章士钊和“甲寅”派,无非是要“用旧习惯、旧道德,或者凭着官办将一切新生力量压下去”。陈独秀为章士钊,这位昔日的“论坛健将,现在也跟着康有为开倒车”,而深深惋惜,他在《向导》上屡屡发表文章,批评章士钊逆潮流而动,尊孔复古的错误言论,并指出:“《甲寅》周报乃是段祺瑞的机关报”,章士钊的《甲寅》,“现在不恭维段祺瑞,这周报哪来的经费出版,而且教育总长的位置又如何保得住”?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人民举行爱国游行示威,队伍行至段政府门前,遭到血腥镇压,死亡40多人,伤150余人。鲁迅称这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时在上海的陈独秀来到亚东图书馆,气恼地自言自语:“秋桐啊,你怎么如此堕落,竟然向学生开枪。我俩从小一道革命,你现在怎么这样的糊涂,我和你绝交。”他把写好的信封好,嘱咐汪原放将信寄出。
危难情真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中统特务逮捕。自“三・一八”惨案后,陈独秀和章士钊已成了政治上的对手,后来又各自奔波,天北地南,几乎断绝了音讯往来。章士钊后来远离政治,而成为闻名上海的大律师。当他在报上得知陈独秀又吃“官司”的消息后,心情尤为沉重,算算这是他这位好友第四次蹲大狱了。回首往事,历历在目,章士钊感慨良多。他知道陈独秀是请不起律师的,而一般的律师他也不会接受,于是便自告奋勇前来南京,担任陈独秀的辩护律师。当章士钊前来探监时,陈独秀紧紧握住章士钊的手,连连说:“难为你了。”次年四月,江苏省高等法院在江宁,对陈独秀等人案件进行三次公开审判。公审的消息传出后,参加旁听的人一次比一次多,《申报》是这样报道的:“唯庭地不敷容纳,后至者多抱向隅,有立于座次两旁者,有立于记者席之后者,有立于室外者。”当法官宣布开庭,陈独秀在法警的押解下走入被告席时,庭内顿时寂静无声,众目睽睽之下,陈独秀镇静自若,面带笑容向旁听席的各界人士颔首致意。
检察官宣读的书说,陈独秀等“主张打倒国民政府,和无产阶级是一样的目的,都是共产,都是危害民国”,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在陈独秀作完抗辩后,章士钊从辩护席上站起,开始了他洋洋洒洒五千言的辩护。“本案为首本严言论与行为之别。言论者何?近世文明国家,莫不争言论自由。……要之,以言论反对,或攻击政府,无论何国均不为罪。陈独秀之暴动,谓与打倒北洋军阀时所用之策略正同,核之恒人心理中之杀人放火,相去甚远。……综上所言,陈独秀之主暴动,既未越言论或理想一步,与紧急治罪法上之“行为”两字,含义迥不相侔是以行为论,独秀亦断无科罪理。……所谓叛国危害民国及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同之主义,湛然无据,应请审判长依据法文,谕知无罪,以保全读书种子,尊重言论自由,恪守法条之精神,省释无辜之系累。”章士钊已经说的口干舌燥,可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陈独秀并不领情。当章士钊说到“托洛茨基派与取犄角之势以清共”时,他再也耐不住性子,几次欲站起来,都被法警按住。章士钊辩护完后,陈独秀便站起来发表声明说:“章律师等之辩护,以其个人之观察与批评,贡献法院,全系其个人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
章士钊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绞尽脑汁所作的辩护,陈独秀不仅毫不领情,还将自己逼至尴尬无趣的境地。有好事的人曾向他谈及此事,他只是笑笑说:“我弱冠以来交友遍天下,唯有三人难交,陈仲甫便是其中之一。但是,大家相知有素,朋友关系始终如初,故而从无诟谇。”陈独秀原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后又改判为八年。当时《实报》报道,陈案全赖章士钊之力,方“得免于死,而判刑八年”。这种议论显有过实之言,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章士钊的辩护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33年5月,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将陈独秀案件的文字材料汇编成册,印刷发行书名为《陈案书状汇录》,主要收录章士钊《辩护词》和陈独秀《辩诉状》。这本书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的辩诉深谙法理,逻辑严密,且又文采飞扬。上海沪江大学和苏州东吴大学还将其选为法律系教材。
可是,陈独秀对章士钊的辩护始终不满,尤其对其中的一些段落,越看越不顺眼。章士钊并不责怪陈独秀,他到上海后,特意来到亚东图书馆,拿出一些钱存放于此,告诉汪原放得便时可带去给陈独秀贴补牢中生活。7月,陈独秀在狱中胃病复发,而法医又治不好。于是,陈独秀又致函章士钊,请他务必让上海中医黄钟来南京一趟,此人曾常给陈独秀治病,深知其脉理。章士钊因手头事务太多,不得陪其来南京,便委托汪原放陪同,他让汪原放带上信函去见黄钟。次年9月,陈独秀又给汪原放去信,并捎去宣纸一张,请即送交章士钊写一条幅,意在“拟择朋友中能书者四人,各书一幅,合为一小屏,朝夕瞻对,以释消愁”。章士钊便写了一首诗,让汪原放转赠。
陈独秀听从老友的劝告,真的在狱中做起了学问。他写了篇《老子考略》的文章,转存于章士钊处,委托他得便“售诸书局出版”。陈独秀似已进入写作的状态,用他的话说,“拟谋中国学术长足之进展”以“制造中国五十年新政治学术之结晶,以谢国人”。
抗战爆发后,陈独秀提前释放,一家人迁居四川,过着清贫的生活。章士钊此时在重庆,偶有闲暇便来看望,并给予生活帮助。1940年2月,陈独秀老病复发,艰难之时,章士钊又慷慨救助。当陈独秀从老友杨鹏升处收到章士钊的汇票时,再也抑制不住感激的心情,立即给杨鹏升去信说:“顷接行严兄由渝转来十六日手书并汇票三百元一纸,不胜惶恐之至。”晚年的陈独秀走着一条极为崎岖的生命之旅,如果没有北大同学会的关心,如果没有象章士钊这样的朋友的理解和资助,他恐怕早已走到生命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