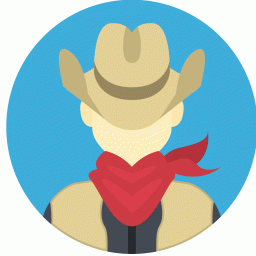李磊散文一组
时间:2022-05-11 07:12:14

一件但求玉碎的瓷
一尊瓷器,从历史的深处流转到我的手上。我与它对视了三年,但我读不懂它。我不知道在它身上发生了多少故事,但我能感觉到瓷器在说话,没日没夜的,像倾诉着一件心事。
我和它是有缘的。三年前,我的一个急性子朋友正值中年便匆匆辞世,成就了我与它的缘分。朋友是因车祸离世的。我得到消息时,感觉中午的太阳突然从头顶落了下来。我和其他几个朋友从地球的不同角落去看他,看他已化作粉尘缩在一只雕花的盒子里。
在为友人动迁的那一天,皖南下起了叫人心都要霉烂掉的雨。山路曲折泥泞,仿佛只是触手可及的距离,我们在雨中走了两个小时。我们把友人安放在前山坡的某棵茶树下,然后,我狠狠地记下了那株茶树的样子。
那株茶树的位置,是友人的父亲为自己选的。友人的父亲说:“我原本希望自己以后能住在那里,一抬眼就能看到家。”而现在他把那个位置让给了儿子。果真,从那株茶树的位置,一抬眼就能看到那栋小木楼;当然,站在那栋小木楼上,毫不费力地就看到了山坡上的那些茶树。
我们在送朋友的时候,他的父亲走在最后,回来的时候,他仍然走在最后。雨水淋湿了他的脸,我们看不出他哭了没有。我们和这个满脸雨水的父亲道别,他从那些在泥地里哭泣的女人里,拉出一位头发同样霜白的老人来送我们。两位老人从泥地里很吃力地走到了木楼前,友人的父亲一一握住我们的手,哽咽着说:“明年清明,茶树就会抽出新芽,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别忘了来采新茶。”
我们泣不成声。一抹眼泪,我看到一尊在黑暗里眨着眼睛的瓷器。那瓷器的光线亲切、柔和,带着忧伤,像友人清晨醒来时惺忪的眼神。我突然决定要把这件瓷器带走,就像带走朋友的一个部分。友人的父亲说:“拿走吧,看了这些东西,我的心就要碎掉。”
那瓷是茶壶,敛口阔腹,垂着双耳;壶在几百年的时光里,因为得到人气的滋养,有了温润的玉质和爽滑的肤质。壶内结了厚厚的一层茶碱,壶柄上系着那枚曾在友人胸前嬉戏多年的小玉兽。显然,这壶是友人生前常用之物。
我把瓷器带回了家,好茶好水地把它养了起来。这一养就是三年。三年里,它一直泛着让我困惑不解的光晕,像有心事,但欲言又止。夏日的某个黄昏,握着那尊微微发烫的茶壶,看着城市上空浓艳得令人窒息的夕阳,我心不安。目光扑朔之时,我看到那些从壶内溅出的茶水,像一颗颗古黄色的泪珠。
我已经错过了三个清明。虽然夏日不是采茶的最好季节,我还是带着那尊根本就不属于我的瓷器,去看远方的那棵茶树。茶树被友人的父亲照顾得很好,高大了许多;而且从木楼到那棵茶树前,已经被踩出了一条小路。我从背包里拿出那尊瓷器,打算把他还给友人的父亲,可山风一推,我身体一抖,那尊瓷器竟从我的手里滑落。
“啪”,好大的一声响,我的心和整个山谷都在打颤。我知道了那尊瓷器只属于一个人,而我,委屈它太久了。
恰似百合
一株百合,开在我的窗台,花的影子开在我的纸上。我知道,无论我在不在意,它都要开放、都要凋落。百合命该如此,谁都改变不了。所以当微风轻拂它,阳光沐浴它,雨露滋润它,我都无法高兴,因为我知道几天后的那个结局。
凋落,是一株百合最凄美、最伤人的时刻。担心它的凋落的过程,便是在等待它的凋落,我有些魂不守舍。于是我想,与其等到那个时刻,还不如现在就凋零的好,还不如不开的好。
比如说幸福。它无论是来得悄然还是来得骤然,我都甘之若饴;无论是走得迂回还是走得断然,我都黯然神伤。因为幸福走了,可我还希望能处在那个幸福的状态,希望远逝的幸福能够失而复得,所以要等待、要回忆、要失意。时间随着指间的香烟燃烧成灰,悲伤在酝酿着神秘的加法,而生命却在进行着简单的减法。我像一株再也不会开花的树,从一个季节的起点,站到另一个季节的终点。于是我想,如果没有幸福呢?就怀着一颗从未幸福的心从生到死,不就没有悲伤了吗?但是,我不愿这样。
比如说爱情。它在我最青春的时候疯狂地掠过了我,就像老宅子着了火,而此劫过后,我废墟般倒在爱的尽头。身边的一切都似乎无关于心,我成了一个空心的人。没有力量再创造爱,也没有勇气去承受爱,我从此与爱情无关。把自己沉默成一泓苦水井,波澜不惊,宠辱不惊。于是我想,如果没有那场爱呢,就是单身或者找一个有些同样心境的女人相守到老,我不去关心她的心情,也不在乎她的容貌,任她按自然的规律在岁月中变丑变老,这样不是少了很多烦恼吗?但是,我不愿这样。
比如说生命。我们的生命总是在自己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就开始了,而我们所做的努力就是在延续生命。如果说努力工作是为了使自己和别人活得更舒坦,可是努力的本身不就是对生命的磨砺吗?如果说生命还有质量一说,那么吃西餐与吃米饭活着有多大的区别?生命的长度摆在那里,任何人的一辈子都只是历史长河里的一滴水,大海少了我的一滴,仍然是漫无边际的。于是我想,与其折磨自己,还不如一辈子平平淡淡算了,把属于自己的时间打发完,再把人类的基因向下一个站点传递就算完成了任务。但是,我不愿这样。
窗台的百合凋落了,纸上百合花的影子也随之消失,百合又回到它从前的样子。但是百合无憾了,因为开放不就是它存在的目的吗?同样,我也无憾了,因为我真真实实地活过、爱过、幸福过。
母亲的河流
不知是什么力量让我记下了这个场景:母亲灌溉苞谷时,俯身在淮河里喝水,貌似平静的河水在母亲的身体里激荡出波涛的声响。尔后,母亲从淮河里走来,满脸都是幸福的红色。
母亲就用她淮河水般的乳汁喂养我,我在母亲的乳汁里吸吮到了淮河的味道。那是一股水草的、鱼蚌的甚至是淤泥的混合味。在贫困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厌倦了高粱、红薯、苞谷面里的霉味后,母亲的乳汁是我日日必不可少的美食。
我迷上了淮河那微微泛腥的味,在我的童年时期,不断向母亲索要品尝淮河的机会。到了1977年,母亲代替体弱多病的父亲去工地上挖河。母亲干的是男人的活,得到的却是半个男人的伙食,营养匮乏的她几次在工地上晕倒。三个月后,母亲她们硬是在平地上开挖出一道深达十米的引水河。完工那天,母亲抱起了我,说:“回家喽!”母亲把塞到我的嘴里,但我却吸吮不到乳汁,我吸吮到的是几滴酸涩的苦水。原来母亲的河流干枯了,我从此失去了品尝母亲乳汁的机会。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几个孩子都到了需要疯狂吃粮的发育期,可家里的几亩土地又连年遭洪水,所以寅吃卯粮是年年都有的事。没有办法,我们便开始吃淮河里的水草。母亲研究了一种吃法,把打捞上来的水草洗净、晒干、切碎,然后加上少量的面粉和盐,用水调成糊状,贴在铁锅里,烧成又酥又香的草饼子。这种吃法流行开后,浅水区的水草便被吃光了,母亲便冒着被汛流冲走的危险,游到淮河中间去打捞。在那困难时期,母亲就用草饼子养活了我们一家人。
为了生产更多的粮食,母亲在河堤外开垦了一块荒地。母亲一心扑在那块地上――地旱了,便从淮河里背水去浇;地涝了,便想方设法把水引出来。为了维持生活,母亲还对我们几个孩子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姐姐帮助父亲负责河堤内土地的管理,我负责在浅水滩捕鱼虾补贴家用,妹妹负责日常家务。那年起了内涝,母亲开的荒地被淹了。母亲说:“要是有块安稳的土地多好,想吃什么就能种什么,种什么就能收什么。”
后来,我们真的有了这样的土地。政府对淮河进行改造,我们被移民到远离淮河的平原深处。这样推门见淮河的日子就没有了,我们真的过起了种什么就能收什么的安稳日子,可母亲却说自己过得不畅快,她总是借回娘家的机会,故意绕道去看淮河,回来后就是一脸幸福的红色。母亲老得自己不能去看淮河后,便让我替她去看淮河。待我回来,母亲会问:“淮河还是老样子吗,水多不多,水草多不多?”虽然现在被改造过的淮河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淮河的味道也发生了变化,可我还是说:“淮河还是老样子,水多,水草也多。”这样母亲便会很宽心,因为“水多、水草多”才是她心中的淮河,才是她想要知道的淮河。
又一次奉母亲之命来看淮河。淮河,静静地横在眼前,怀着三分之二的水。夕阳中,它散发出叫我联想起母亲乳汁的不饱和香气。我突然想起别人问我的一句话:“为什么你身上总有一股水草味?”我想,那是因为我从母亲那里继承过来一条河流,这条河流潜藏在我身体的深处,三十多年来一直在我的血脉里奔流不息。
苦心茶
去年岁末,我病卧在书房里赏雪。友人突然破门而入,披一身雪。他从嘴里喷了一口白汽问我:“那包叶子喝了没有?可以治你的病。”我拂掉脑袋上的灰尘,才想起春日他送我的那包茶。我将茶找回,放在茶几上。友人撕破枯黄的纸包,捏几颗冰冷的叶子放入杯中,再从咆哮着的壶里注入恶狠狠的水。友人安静地趴在热气蒸腾的杯子前,满心期待地等,紫色的头颅像幸福的陶器。
屋外雪正浓。从树枝上落下的积雪,跌出了一地的叹息。我的目光正随着雪瓣起伏时,感觉有股与心境相似的苦香从身后悄然袭来。顺着香气,我看到了那只凝重的釉玉杯,看到了那杯在默默宣泄着它心情的茶。
友人不无得意地笑,一脸的沉醉。我要过那杯茶,看这平平的一杯水竟被绿叶涨满,那浴在汤水里的片片嫩芽,如古丽人的一场酣睡刚醒,舒展着躯体,体态轻盈地停泊在你的面前。轻轻捏起一柄叶子,看。它,孤独、冰冷、凝重、高贵;它,平静、悒郁、含羞、若有所思;它,有着翡翠的颜色、玉石的沉默和莲子的幽心。纳一枚入口中,便觉得其重重心思在舌苔上慢慢释放出来――先是淡淡的苦,旋即浓烈如胆,沁人心骨。苦味淡去后,唇齿间始有暗香袭来,其味诡秘,叫人掉魂。呷一口茶水在唇舌间细细品味,觉得水体殷实韧软,如丝绸饶舌,叫人不忍吞咽;其滋味铺天盖地,叫人心神难安。茶水滑入腹中,一股暖气暗暗生成,顿觉神清气敛,身轻腰软,语言芬芳。
以为这莫测高深的茶必生在幽谷深山,经霜臂玉指采摘,焙自贫道苦僧。友人淡然一笑,说茶树生在他老家的祖坟坡,采茶人是他自己,焙茶人是他的老父亲。我十分惊愕,恍然想起年初落宿于友人故乡的那个春夜。
那次和友人在南京出差,归程时,友人携我绕了几百里山路去看他的哑父亲。到那村落时,已是夜半月沉。友人的父亲应声开门,他的脸与夜色相融,只有眉骨高耸着,瘦弱的身影在油灯下时现时隐,飘忽不定。老人在青灰色的夜里走动时,脚步轻稳如猫,只有身上骨头和身边器物的撞击声格外清脆。
老人为我们打扫好屋子,又抱来厚厚的被褥将床铺好,然后双手在胸前舞个不停。我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但我能看出老人很兴奋。尔后友人扶他的父亲一起朝夜里走,油灯随着山路的转折而明灭,藏青色的夜空下,四周都是鱼脊般连绵起伏的山峦。我在雕花木床上睡到半夜,被楼下灶房里传来的幽幽苦气熏醒――原来是友人和他的父亲在焙茶。
朋友叫我给这茶起个名字。我望着那胆色的点点绿粒,想起两个字:苦心。“就叫‘苦心茶’吧。”我说,“没有一颗数十年沉静、孤寂的心,是焙不出这么古气磅礴、苦彻人心的茶的。”友人竟悄然滑泪。
雪在掩埋着屋外的世界。寂静的空中时时传来枯枝断折的惊人声响。我静静地捧着这杯苦心茶,想着那个夜半焙茶的老人,想起他满身的风骨以及那在风中抖动的白眉。
裸奔的鹰
这些年里,我家乡的平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荒山丘和野树林没有了,它们消失的地方密不透风地站立着庄稼丛。世世代代的人都在努力地对平原进行着改造,终于这种改造达到了极限:平原平坦得没有一点褶皱,像一张省略掉五官的脸。
庄稼们貌似斯文地占领了平原的所有陆地和水地,本性疯狂的野草在庄稼的空隙里苟且偷生。一年四季,庄稼的长势代表了平原的表情:油菜花开了是春,谢了是夏;玉米叶黄了是秋,灰了是冬。日子变得有些单调起来。
生长在记忆里的荆藤、野花,开始变得难得一觅。我年少时嗜爱的野辣菜、小豌豆在阔叶除草剂被疯狂使用的年代里,再也难寻踪迹。偶尔起了童心,带着孩子,挽着篮子,趁着春光去挖野菜。我们几乎踏遍了这个平原上所有的麦地,除了找到那种已变得和小麦脾气相仿的荠菜之外,便再无收获。我们用荠菜包饺子,却在饺子里吃到了麦苗的味儿。我仰在椅子上长叹,难道我们的吃食已逃不出麦子的包围?
平原上的河流胆怯了起来,再不是从前那个放荡不羁的样子了。它们在这几十年里不停地收缩着自己。原先的一道深莽大沟,现在我单腿便能跳跃过去。河流也开始没有城府起来,我父亲年轻时须扎猛子才能到达底部的河流,成了我卷起裤腿耕作的稻田。原本曲折贯通的平原水系,懒惰了,黏稠了,窒息了。十年前一村落杏花,十里河道飘杏花的情景当然没有了。河流变得沉默,缺少情调,没有激情起来。
村西原本有块山冈,那儿是这块平原离天最近的地方。我的整个童年都乐此不疲地进行着一种游戏:骑着羊羔爬上山冈,然后再顺着山坡一滑而下。可我的父辈们需要更多的粮食来维持家庭,山冈便在那一代人的努力下被夷为平地。可那些在山冈上安家的山雀与乌鸦便从此没有了归宿,它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村落上空漫无目的地盘旋,天黑都不愿落下来,我真为它们揪心。
真正以平原为家的动物也少了起来,原本惊蛰后蛙声震天,谷雨后布谷催人开镰的场景,被家禽的聒噪声取而代之。檐下的燕子巢依旧在,可那些穿着绅士服的燕子却没有了踪影。我们身边是那些体态臃肿、拙翔的鸟――鸡、鸭。天空因为缺少鸟的飞翔,而空白、寂寞了起来。
当然,我们的生活仿佛是越来越好了。庄稼们都丧失了理智似的疯狂生长,为我们提供着吃不完的粮食。我们在平原上大量饲养着那些符合我们胃口的动物,并为它们提供了没有天敌的生长环境。狼、野猪和狐狸等动物和我们的祖先打了几千年游击战,终于在二十年前,被我的父辈们从平原上一举歼灭。现在这样的命运又轮到了鹰。
其实,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在平原上看到鹰了。那天我钻到一块正值青春季的玉米地里给玉米追肥,偶遇了这只鹰。它为了摆脱我的追捕而拼命奔跑,以至于身上羽毛抖落了一地。很显然,它的翅膀有伤,不知是不是枪伤,让它从此告别了天空、告别了飞翔。它身上的羽毛脱落得厉害,整个胸部显露无遗,我又估计它是受到了化肥或农药的灼伤。我把它养在鸡舍里,它用一种很伤人的眼神盯着我,一直到死。当然,它拒绝了我喂给它的所有食物,这是它的骨气。
我不明白,是鹰进化得太慢,不再适应我们的平原,还是我们的平原进化得太快,已打算把鹰淘汰?无论如何,在这个连鹰都裸奔起来的年代,我只能祈求眼前的幸福生活不要走得太快。
作者简介:李磊,男,70后,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结集出版。近作发表于《散文》、《清明》、《北方文学》、《岁月》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