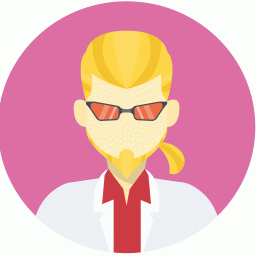张翼鹏:奔赴大自然的苍凉之约
时间:2022-04-30 01:06:09

小时候,我舅舅是个农村的摄影师,就是走家串户给人家拍照的那种照相师傅。所以我很小就接触过双镜头的老式海鸥120照相机。每次去舅舅家,最愿意做的事情就是看舅舅鼓捣相机和冲洗黑白照片。我爷爷是我们当地的文化名人,他接触的朋友中有很多是搞摄影的,借此机会我也认识了其中的几位,很羡慕他们手中的那些专业器材,那时候能有一张彩色照片,对谁来说都是很兴奋的事情。
高中时,我终于整了台海鸥DF-300,买最廉价的乐凯胶卷,天天屁颠屁颠地到处乱拍,那台相机一直用到我上大学。后来去周庄写生还是用的那台相机,只是胶卷从乐凯换成了柯达。那时的水乡婉约、宁静,五月的周庄被成片成片的金黄色油菜花海包围着,如诗如梦,烟雨迷蒙的江南和着温婉缱绻的吴侬细语如一幅水墨画一样印进了我的胶片,也印进了我的记忆。那个春天,很少远行的我突然发现,原来外面的世界这么美,从此我发疯一样爱上了旅行。前些日子还翻出那时拍下的周庄,看着那些熟悉的画面,那些旧日时光如水一样漫过记忆,似乎我的身边又响起了悠扬的吴歌,似乎那江南小镇的炊烟再次在记忆中氤氲开来。
那个时代,进藏是一种疯狂的行为
上世纪90年代的文艺青年,都有“嬉皮士”的范儿。读艺术院校的我们,把头发留得很长,穿着翻毛大兵鞋,走起路来,长发飘扬就像一阵风。而那时对喜欢摄影的年轻人来说,西部有着很强大的魔力。现在我们看西部题材的摄影作品看得太多了,似乎有些审美疲劳,那时候不一样,某位摄影大师如果拿出几张采风的“大片”,足可以轰动摄影圈。
于是我们几个“臭味相投”的同学,在毕业考察时毅然选择了去,那是一个疯狂的决定,22天的西部之旅,让我脱胎换骨,从此对旅行摄影“严重发烧”。
去之前,我花5500元买了佳能EOS1000胶片机,上世纪90年代的大学校园,花五千多元败个单反相机绝对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那是一个大学生一年的生活费。但因为对摄影的热爱,还是忍痛买了,带着我那架宝贝相机,1995年8月初,我们登上了西行的列车,没有冲锋衣,没有登山鞋,只有热血沸腾,激情澎湃。那次的旅程是极其艰苦的,当时的青藏线路况很不好,到处都是损毁路段。从西宁到格尔木,再从格尔木到拉萨,一路历经艰险,终于到了朝思暮想的雪域圣城拉萨。
路上有几个情节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一是独特的高原反应,别人高反是头疼,胸闷,我不一样,我是肚子疼,老想上厕所。当时长途汽车从西宁出发,一路在戈壁中穿行,从天亮走到暮色四合,再到夜如浓墨,远处的地平线飘飘忽忽,近处的骆驼刺影影绰绰,犹如鬼魅。而在这样一个诡谲的夜晚,我蜷曲着身子,腹痛如刀绞。我喊司机停车想方便一下,藏族司机说,不能停,让我看看窗外。我向窗外看去,夜色笼罩的戈壁滩异常沉寂,但夜幕之中却有几点绿光伴随着我们的汽车快速移动,我下意识地问,“什么光?”“狼的眼睛。”司机漫不经心的回答让我毛骨悚然,倒吸一口凉气,那一直移动的绿光竟是一群戈壁狼。一直忍着剧痛总算到了一个有灯光的地方,是个武警部队的兵站,司机才终于敢停车,狼是怕光的,一般不会跟过来。
经历了一个无眠之夜,天放亮时车子闯入了一个小城,我们似乎从月球重返人间,我记住了这个小城的名字――格尔木。小城的街道干净整洁,中间的绿化带内盛开着大片大片的格桑花,街上行人极少,异常安静,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小城,当时就梦想如果可以居住在世外桃源格尔木,该是多么惬意的事情。
8月在山东,骄阳似火,而8月的昆仑山口却是鹅毛般的大雪弥天漫地,能见度不足半米,车灯光柱照射下,目之所及全是纷扬的雪花,车子如蜗牛一样爬行,随时都有可能滑进深谷。到了五道梁,汽车竟然抛锚,司机顶着暴风雪下车修车,而我们则把全部能穿的衣服都套在身上,于半梦半醒之间熬到了另一个天亮,清晨车修好了,我们也几乎冻僵了。
就这样,历经磨难,经过六天五夜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从济南到了拉萨。对于现在来说,青藏线是难度系数最小的进藏线路,但那个时候,却是生死磨难。当布达拉宫终于出现在我们的视野,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之后的十几天,我们不知疲倦地用手中的相机拍摄着我们心中的。从未见过的草原雪山,从未见过的蓝天白云,天籁般的经声,飘扬的经幡,一场视觉的盛宴彻底让我们迷醉了。那时候,校园里正流行郑钧的《回到拉萨》,对于我们那些摄影爱好者来说,当时的感觉就是,梦里的,我回来了。
那次进藏回来,我们在山东艺术学院《名人画廊》举办了一次《青藏行》摄影展,展厅里播放着我们从拉萨带回的藏族音乐,参观者络绎不绝,反响很大。
后来我一发不可收拾,数年间,走遍了西部的山山水水,手中的相机不断地更新换代,从胶片到数码,我们不再吝啬手中的快门,每次走进风景中随心所欲地记录,真是感觉酣畅淋漓。
稻城亚丁,我身在天堂却去地狱走了一遭
现在回忆起为了风光摄影而经历的那些苦难,似乎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相信每个走在路上的摄影人,都是痛并快乐着。第一次进藏的时候,除了腹痛,我几乎没感觉到高反,以至于让我很看不起别人的高反。但后来去亚丁,去五色海回来后却有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后来回想有几个原因,在海子山上看见奇特的低空云,我忘乎所以,在海拔5200米的高度疯狂奔跑着摄影,体力的透支埋下了隐患;后来在亚丁爬山的时候,一路经历了雪、雨、冰雹,全身湿透,受凉了,有点感冒。在高原感冒是很可怕的,容易引起肺水肿。当时我躺在藏族老乡家里,已经几近昏迷。地板下不时泛出一阵阵牦牛圈的臭气,混合着酥油的膻味,一种独特的混合气体在小屋子里弥漫着,天还在下雨,屋顶居然断断续续地漏着雨水,我蜷缩在床上,靠着墙,浑身哆嗦,一次次地出现幻觉,几乎不知身在何处。后来同行的驴友花200元喊藏族老乡熬了一锅鸡汤,我吃不进肉去,勉强喝了3碗鸡汤,却奇迹般地缓了过来,我从地狱再次回到人间。感谢亚丁的那只鸡,牺牲自己拯救了我。后来和当地人聊起这个事情,他们说当地高海拔山地生长的鸡,吃的全是松茸等高海拔食物,肯定体内有抗高反的一些微量元素,所以亚丁的鸡应该可以治疗高反。或许是调侃,但我却真的恢复了体力,等回到稻城,完全痊愈,租辆自行车,几个弟兄又在稻城乡村骑行了一把。
稻城亚丁,从地狱到天堂,但海子山的疯狂奔跑却让我拍下了几张很满意的风光片,纵使高反也无悔啊,我为摄影狂,高反算什么,呵呵。
坝上,为一只鸡而改变的行程
我总是只确认一个旅行目的地,就上路了,走到哪算哪,天黑了,找个小镇住下,就是我与小镇的缘份,不是因为旅行,可能我一辈子都不会到这个小镇来。人与人有邂逅,人与城镇、与村庄也有邂逅,而这种邂逅是旅途中的最大的乐趣。
有一次去坝上拍片,蓝天白云之下,我们的汽车在路面上飞驰,突然无意中撞死了一只横穿马路的鸡,远处几个村民气势汹汹地朝我们奔了过来,因为以前多次看到在坝上被恶意敲诈的新闻,这次撞死了人家的鸡,虽心含愧疚,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我们慌乱之下掉头择小路仓皇而逃,而我们选择的小路只是一条护林路,就这样一头扎进了深山老林。一路无人,群山连绵,森林肃杀。突然前方路上迎面驶来一辆摩托车,后座上还载着个精壮男子,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何来行人?如同孙悟空遇见了深山中妖怪幻化的老妇,我们心生疑窦,会不会是刚才的村民抄小道前来截我们了,不由得紧张起来,但别无退路,只能硬着头皮开过去,摩托呼啸着就和我们交错而过,原来是虚惊一场(但现在想来那摩托也好生怪异)。后来一直走到天黑,也不曾再见一车一人。从下午走到晚上11点,我们的车如一只深海中的鱼游动在浓浓的夜色里。突然远远地看到一点灯光,总算有人烟了,我和朋友在一家颇有黑店风范的小餐馆里伴着两个喝闷酒的东北大汉胆战心惊地吃了一顿晚餐,后来老板领我们找了个住处:一个低矮的民房,其脏乱不亚于济南天桥下乞丐栖息的场所。朋友凭借很强的意志力躺下了,而我选择躺在车里看星星,半夜冻得几次醒来,后来干脆躺在车座上迎接黎明,从黎明前的黑暗到晨曦初露,再到旭日东升,我第一次完整地感受了一次黎明。天亮后,才发现我们住的这个小村只有四五户人家,它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叫“青石砬子”。
现在说起这些旅程中的意外,俨然是一种乐趣,如果没有这些偶然,何来让我们回味无穷的旅程。旅行的魅力也许就在于其偶然性和不可预知性吧。
人近四十,依然有梦
从1993年开始旅行到今天,我游历了大半个中国,现在对旅行摄影的痴爱有增无减,而如今我把目光投向了世界,环游世界的计划已经启动。人近四十,早已过了做梦的年龄,但我依然在梦里沉睡不醒。我会继续走下去,让人生有更多的注脚,让梦继续飞翔,行者无疆,我会永远在路上。
我想等我老了,我不会躺在床上翻看那些我拍下的风景,我要回到风景中去,回到在那些梦想中的地方。正如那首歌里唱的,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那风景里……
摄影师介绍:张翼鹏,男,1973年生于山东莒县, 1996年毕业于山东工艺美院装潢设计系。大学毕业后画过插画,做过美编,搞过企划,当过老师,现任某传媒公司总经理。十余年来,足迹遍及大漠戈壁、雪山高原。喜欢人文地理题材的摄影,并乐此不疲,深深迷恋。有数百幅绘画、书法、摄影作品,多篇诗歌、散文、游记见诸于各类报刊杂志。
摄影器材:尼康D3及系列镜头
朋友眼中的侠客张
郁青:他身上找不到都市的气息,浑身透着“大漠孤烟”的风范。他是一个喜欢行走的人,喜欢一个人上路,做无牵无挂游弋在天地之间的剑客。
天涯孤旅:他的办公室到处摆放着从各地旅行带回的物件,这家伙拿这些东西当宝贝,看得比命还重要。他说,每一件物品背后都有一段故事。他一有空就往那些苍凉、没有人烟的地方跑,或许只有那里才能盛放他张扬的灵魂和狂放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