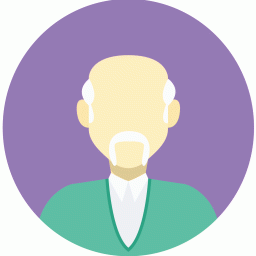不仅是“匕首”,不仅是“投枪”
时间:2022-04-29 11:17:35
摘要:鲁迅的“杂文”不是政治判决,而是别一样的“文学”,作为文学家的鲁迅的一生就是“杂文的一生”,其杂文的历史“过程”性折射了鲁迅本人的思想成型与丰富。行走于“杂文人生”中的鲁迅,同时又通过对“杂文”的写作实践不断体悟“文学”的意义,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观念。作为“杂文人生”的历史过程,鲁迅的文字从一般文明现象的批评发展而为整体制度的对抗,而在文字演变的背后,则是在现实社会各种阶层和群体中,不断寻求自我认同与差异甄别的思想过程。
关键词:
杂文人生;文学观念;文明批评;制度对抗
中图分类号:I21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1)05-0071-07
对于鲁迅杂文,长期以来我们几乎恪守“匕首”与“投枪”的比喻,用以突出鲁迅面对黑暗世界的批判态度,其实,置身“杂文世界”的鲁迅也相当的丰富,“杂文”不是政治判决,而是别一样的“文学”,其中不仅只是结论和判断,更有自己“过程”和“发展”,除了批判的犀利,同样也有人生与文学的曲折思索和探求,有自我从沉吟到奋起的选择和转变,“匕首”与“投枪”的生动内涵,也只有置放在如何“杂”起来的“过程”之中,才有更为准确的说明。
鲁迅最早的杂文发表在1918年9月《新青年》5卷3号的“随感录”专栏,至1936年10月17日逝世前二日作绝笔《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他自我总结:“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可以说,杂文伴随了鲁迅的一生,或者说,作为文学家的鲁迅的一生就是“杂文的一生”。拥有“杂文人生”的鲁迅,怎样在这一过程中寄寓了自己的感念,暗含人生的选择,包括对自己从事的文学的地位呢?
透过“杂文人生”看鲁迅对人生和文学的选择,将是一个独特的视角。
一
鲁迅杂文的历史“过程”性首先体现在它作为《新青年》整体思想工程的“过程”性,也就是说,鲁迅杂文是在《新青年》群体的思想启蒙设计中逐步脱颖而出的,这一过程既标志着《新青年》思想群体的成熟发展,同时也折射了鲁迅本人的思想成型与丰富。
以“随感录”命名的最早的鲁迅杂文,本来是新文化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随感录”并非鲁迅别具匠心的个人创意,而是《新青年》总体策划的一部分,最早的“随感录”出现在1918年4月《新青年》4卷4号上,共七篇,由陈独秀、陶履恭、刘半农分别撰写。这些“随感”,直到1919年5月6卷5号第五十六篇重新命名《来了》以前,均没有另外命名,一律以统一的编号代替,作者署名也不像其他长篇大论般赫然置于篇首,而是附缀于篇末的括弧之中。这都体现了《新青年》当时的总体办刊意图和对于这类杂感的初步定位。这一类作品,往往针对具体的社会世态,有感而发,既短小精悍又泼辣犀利,亦庄亦谐,亦文亦白,似乎最能承担新文化推行中那些广泛而复杂的“社会启蒙任务”,大约正好符合了《新青年》编者最初的集中同人力量开展同一方向工作的思路。“随感录”的启蒙任务本来就是他们众多同人的“集体”工程,代表了《新青年》系列计划的一部分,因此完全可以用统一的编号标注之。
鲁迅的杂感是以《新青年》系统工程一部分的身份出现在新文学史上的,这也清晰地表明了鲁迅这一文体的写作在一开始就从属于现代中国思想启蒙的潮流,至少在上世纪20代的前期,以《新青年》“随感录”为代表的思想启蒙主要是集中于中国社会的“文明批评”,自然,这也理所当然地成了鲁迅的杂文的重要内容。鲁迅说:“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
但鲁迅终于在群体性的“随感录”阵营中脱颖而出了,《新青年》“随感录”一改旧例,换以独立的命名,正是从鲁迅的《来了》开始的,这在一定的程度上说明鲁迅杂文成熟的程度足以以更加个人化的方式存在了,同时也表明《新青年》内部整体的思想与文学的个性化色彩的加强。当然,一个在思想上各自独立的思想群体的进一步发展也许就是彼此分歧的出现,这是历史变迁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像鲁迅这样的作家不断提炼人生体验,磨砺自我思想,走向更加独立的思想追求的必然要求。
二
行走于“杂文人生”中的鲁迅,同时又通过对“杂文”的写作实践不断体悟“文学”的意义,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观念。
在最初,鲁迅对于“杂文”、“杂感”这一文体的评价颇为审慎和低调。1925年11月,鲁迅在《热风・题记》中说:“所以我的应时的浅薄的文字,也应该置之不顾,一任其消灭的;但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存留,给我编辑起来了。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杂文被喻为“疮疖”。1925年12月,在《华盖集・题记》中,鲁迅说:“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杂文又被称为“无聊的东西”,从“创作”中除名。1926年10月,鲁迅在《华盖集续编・小引》中说:“这里面所讲的仍然并没有宇宙的奥义和人生的真谛。不过是,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了下来。说得自夸一点,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时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现在更不想和谁去抢夺所谓公理或正义。你要那样,我偏要这样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头是有的;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也是有的,此外却毫无什么大举。名副其实,‘杂感’而已。”浅薄、偏激,不能全然说是作者的自谦。1926年11月,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鲁迅说:“记得先已说过:这不过是我的生活中的一点陈迹。如果我的过往,也可以算作生活,那么,也就可以说,我也曾工作过了。但我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不过我曾经尝得,失望无论大小,是一种苦味,所以几年以来,有人希望我动动笔的,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给来者一些极微末的欢喜。人生多苦辛,而人们有时却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这样的工作。然而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
比方做土工的罢,做着做着,而不明白是在筑台呢还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筑台,也无非要将自己从那上面跌下来或者显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在这里,对“非华美”的文字的叹息依旧,不过,又增加了一种自我人生的满足――在“创作”之外的“人生”寻找新的文字的价值,是不是鲁迅的新思路?1927年的《三闲集・怎么写》表示:“有时有一点杂感,仔细一看,觉得没有什么大意思,不要去填黑了那么洁白的纸张,便废然而止了。好的又没有。我的头里是如此地荒芜,浅陋,空虚。”又一次提到了荒芜、浅陋与空虚。
然而,就是在以上审慎和低调的同时,鲁迅也不时流露出一种敝帚自珍式的倔强,这或许就是来自内心深处的自信。关于《坟》,他同时又表示:“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还有愿使偏爱我的文字的主顾得到一点喜欢;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吐,――我自己知道,我并不大度,那些东西因我的文字而呕吐,我也很高兴的”。关于《华盖集》,鲁迅说,虽然杂文反映了他“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怕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
越到后来,在鲁迅近于自我调侃的语气中也越包含了更多的倔强、固执与坚定。1935年12月,在《且介亭杂文》的《序言》里,鲁迅回溯历史,用整整一大段的篇幅为“杂文”正名: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在这里,鲁迅的文学观念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换:杂文不仅自来就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更关乎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写到这里,鲁迅显然是激情澎湃了!
显然,鲁迅已经越来越多地认同和欣赏着这一“纵意而谈”的文体,并且不断将自己最丰富最生动最敏捷的思考寄寓其中,30年代初出版的几本杂文集――《三闲集》、《 二心集》、《南腔北调集》干脆以他人对自己的攻击作为书名,显示了鲁迅此时此刻对自身文字力量的充分的信心。1933年10月结集出版的《伪自由书》,将文中涉及到的论争材料,“都附在我的本文之后,以见上海有些所谓文学家的笔战,是怎样的东西,和我的短评本身,有什么关系”。1934年12月结集出版的《准风月谈》、1936年6月出版的《花边文学》都“将刊登时被删改的文字大概补上去了,而且旁加黑点,以清眉目”。1937年出版的《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也做了类似的处理。鲁迅自述说:“即此写了下来的几十篇,加以排比,又用《后记》来补叙些因此而生的纠纷,同时也照见了时事,格局虽小,不也描出了或一形象了么?――而现在又很少有肯低下他仰视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尊脸来,看看暗中,写它几句的作者。因此更使我要保存我的杂感,而且它也因此更能够生存,虽然又因此更招人憎恶,但又在围剿中更加生长起来了。”
杂文,到这个时候,已经成了鲁迅挑战现存制度、捍卫社会权利的得心应手的工具。
三
作为“杂文人生”的历史过程,鲁迅的文字从一般文明现象的批评发展而为整体制度的对抗,而在文字演变的背后,则是在现实社会各种阶层和群体中,不断寻求自我认同与差异甄别的思想过程。
20年代前期的鲁迅杂文主要是他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五四启蒙,表达对一般文明现象的批评:“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而“猛烈的攻击,只宜用散文,如‘杂感’之类”。到了20年代后期,鲁迅对人生社会的认识和对自我的设定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从一个方面讲仍然是他沿着固有的“为人生”思路前行的结果,从另一个方面看,也包含了鲁迅对于新的历史境域的新思考与新抉择,我们也有必要解读鲁迅“最后十年”的这些新的人生体验。这些体验是我们继续追踪鲁迅杂文发展的基础。
如果说,20年代前期的鲁迅是自觉承担了“文明批评”的使命,那么,20年代后期的鲁迅则选择了与现实体制的更加分明的对抗。
这一对抗是在社会的几个层面上同时展开的。
首先是政治制度层面上的对抗。在20年代后期鲁迅的经历中,1927与1928年是十分重要的年份。这两年的风风雨雨继续给鲁迅一系列人生经验,迫使他选择了走向生命最后十年的道路,也因此开始承受了这一条道路上的更大的艰难。1927年,鲁迅被迫南下之后投奔了“革命”大本营广州,却又最终绝望而去,这对他最后十年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于“三一八”事件,鲁迅的用语是“出离愤怒”,对于“四一二”,则称自己“被血吓得目瞪口呆”,“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言语之中,透出了鲁迅始料未及的震惊。鲁迅绝望于中国现代的这些所谓“革命”的政治家,同时,也对当时为所谓“革命”政府服务的中国人(包括中国青年)十分失望。“奴隶们受惯了‘酷刑’的教育,他只知道对人应该用酷刑”,“奴隶们受惯了猪狗的待遇,他只知道人们无异于猪狗”。“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
1927年以后的鲁迅,是行动的鲁迅。也就是说,残酷的现实已经告诉他,仅仅是“彷徨”于个人的感受并不能最后解决问题,现实的活的人生
需要他用“行动”来争取最基本的生存。“行动”就意味着从对世界与人生的冷峻的“观照”转为主动的撞击和投入,不仅要洞察世界的荒谬,还需要出击与搏斗,需要他以自己的方式主动“寻找敌人”,他要靠自己选择对手来扫荡人生道路的阻碍。在这时,鲁迅的生命活动与文学活动始终保持一以贯之的个体独立性,讲“单打”,靠“独斗”(鲁迅曾经讽刺中国人只有“合群的自大”),他的武器也不是群体作战的大炮与大旗,不过就是自己手中的“匕首”与“投枪”。
今天,有一种评论认为鲁迅将文学“堕落”为匕首与投枪,失去了文学性。问题在于什么是“文学”,问题更在于我们必须按照鲁迅自己的逻辑来理解他的“文学”。文学不就是一种人生的极具个人性的话语形式么?其实,“单打”“独斗”所依靠的匕首与投枪恰恰与文学的个体存在方式相一致,而我们今天的更多的所谓“文学”不过是唱响了一个时代主潮所容许的甚至是模式化的东西,更像是没有个性的大炮与大旗,但鲁迅从来就不从属于这样的时代主潮,他使用的不过是自己手制的匕首与投枪。“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于是,便有了匕首与投枪,这是鲁迅的这个“地方”的生存方式,也是他在这个“时代”的话语方式。为了现代的人生,鲁迅选择了这样的话语,这样充分展示人生当下感悟的话语,难道它不就是从内心生长起来的真正的文学吗?
其次是与整个学院派知识分子阶层的对抗。
1927年以后,鲁迅完全告别了“学院”,实现了从学院派知识分子到社会派知识分子的自我转换,从而在更大的层面上表达了与“体制之内”的学院派知识分子阶层的对抗。
由于民间资本力量的薄弱,现代意义的中国教育一开始就属于国家事业的一部分,从晚清“同文馆”到“京师大学堂”,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绝大多数著名高校都属于“官办”。中国现代教育的本质是国家主义的。这直接影响到了教育的思想与教育的管理模式,也影响到了学院之中的知识分子的心态。中国教育的国家主义性质决定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政府当局必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显然更重于他们与国民的关系。中国学院派知识分子这一历史特征使之与西方学院派知识分子大相径庭,也很难生长出如西方知识分子那样的独立批评的精神。在这些知识分子当中,一种远离“知识目标”的新自我异化方式正在形成。
鲁迅发现,学院派知识分子常常举着“公正”、“理性”的旗帜站到政府当局的一边,从女师大事件到“三一八”惨案,《现代评论》派的表现就是这样。而且,更可悲的还在于他们的善变,只要“形势”需要,他们可以由依附北洋政府很快转向反对北洋政府的。鲁迅描述说:段执政有卫兵,“孤桐先生”秉政,开枪打败了请愿的学生,胜矣。于是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们的“公理”也蓬蓬勃勃。慨自执政退隐,“孤桐先生”“下野”之后,――呜呼,公理亦从而零落矣。那里去了呢?枪炮战胜了投壶,阿!有了,在南边了。于是乎南下,南下,南下……于是乎“正人君子”们又和久违的“公理”相见了。
“学者”、“教授”、“正人君子”在鲁迅那里总是充满讽刺意味。鲁迅说得好:
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然而知识阶级将怎么样呢?还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
第三是鲁迅对“革命阵营”的认同与疏离。
在与一个专制政府的对立当中,鲁迅同情的自然是那些受压迫又代表了民众声音与力量的民间民主人士,专制独裁的大屠杀更凸现了共产党存在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共产党以及它的革命活动就这样进入了鲁迅的视野。但鲁迅通向革命、与革命者结盟的道路在一开始就并不平坦。创造社、太阳社的忽然“发难”是鲁迅与无产阶级的文化理论与文学理论正面遭遇,这在他那里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方面,就是这样的理论“压力”迫使“应战”中的鲁迅开始调整着自己的知识结构与文化视野。鲁迅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马克思主义从此成为鲁迅救正“进化论”的新的思想资源。鲁迅的从理论上接近马克思主义直接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开始形成自己的“阶级”视野,从而进一步拉开了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距离;二是奠定了他与后来的左翼文学家进一步合作的信仰基础。另一方面,在鲁迅认识“革命文学”与马克思主义之初,创造社、太阳社如此突如其来的攻击的确给正在寻找朋友与同志的他很大的伤害。这一经历促使他严肃对待自己未来在“革命”联盟中的体验,因为,在这些左翼革命青年这样专断、蛮横的批判中,鲁迅又感受到了中国历史似曾相识的一幕: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二十多年前,都说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实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朝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利害。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
“革命”的大旗之下掩饰着对“主子”地位的争夺,这是多么值得警惕的事实!而且,这样的“革命”还专横得如此的可怕:“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地运用了。再则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鲁迅发表这样的批判性言论之时,左联已经成立,他本人也在冯雪峰等人的劝说、影响下投身于左翼文艺阵营并成了一面当之无愧的大旗。然而,他显然对“革命文学”论争中的体验记忆深刻,并不时咀嚼回味,用作认识当前与未来中国问题的重要根据。有人说鲁迅“记仇”,报复心重,甚至睚眦必报,像这样“水过三秋”的往事依然久久不能释怀,就是证据。其实,我以为,这正是鲁迅的远见卓识:中国现代革命的本质就是改变我们固有的封建奴役关系,恢复人的自由与尊严,如果投身其中的革命者实际却依旧拥有一张专制独裁的嘴脸,这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目睹了从民主“革命”到“反革命”独裁的嬗变,鲁迅不得不对新的“革命同志”提出更加严厉的要求。
30年代,鲁迅已经站在了现实政治体制的对立面,他同样也警惕着出现在现实政治体制的“革命者”那里的自我异化的可能性,他知道,旧的独裁专制的“体制性影响”是强大的,甚至强大到可以最终同化向它挑战的“革命者”。对于鲁迅来说,与体制的对抗,自然就包括了与“革命者”身上的旧体制因素的对抗,在左联成立的大会上,鲁迅的演讲满篇都是忧虑与警觉:
有许多事情,有人在先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我不必再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这是一个多么不“讨人喜欢”的开篇啊!没有慷慨激昂,没有歌功颂德,也没有誓死效忠,因为在真诚地期待着中国革命,热切地盼望着国民自由的鲁迅看来,当下最要紧的恰恰不是弹冠相庆,而是如何保持“革命者”的超越旧传统旧体制的精神境界,他最放心不下的还是专制独裁的“主子”心态: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鲁迅特别提出: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在中国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
事实证明,鲁迅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在左联内部的一些领导人那里,后来的确以“奴隶总管”的姿态执掌革命文坛。为了最大程度地反抗专制体制的一切构成因素,鲁迅不得不成为一名“横站的士兵”。
横站的士兵,虽然还是以“匕首”和“投枪”为自己的常规武器,然而内心世界的痛苦、矛盾、挣扎以及决绝却不是武器本身就能完全概括的,鲁迅的“杂文人生”带给我们启示丰富而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