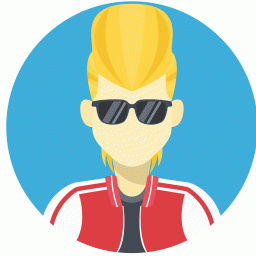“10万+”作品能产生新经典吗
时间:2022-03-09 02:27:53
【前言】“10万+”作品能产生新经典吗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电视将人们的感知世界塑造成一个可以任意显像、任意剪辑并可用画面解读的世界的思想(意识形态),而互联网的客户终端则大大地发展了这种文化帝国主义,它的剪辑和拼接比电视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加片段化、模糊化的图片和情绪化的判断,构成了一个更加不负责任的世界。...

在消费社会,人的一切活动都取决于某种技术结构,原本私人化的阅读领域也不例外。手机、IPAD之类的互联网智能终端近些年来取代电视成为最主要的信息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解救了在电视时代完全依赖于视听和符号传播的人们――手机上安装的各种新闻客户端和朋友圈文章,让文字阅读重新回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传统媒体进入寒冬,微信开放平台让无数优秀的传统媒体人加入自媒体大军,朋友圈文章阅读量动辄“10万+”,这是否意味着文字的回归?新闻客户端、自媒体的时代,诸如咪蒙《致》、《致low逼》等网文能否如唐诗宋词一样,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经典?
试想一个场景,前一秒钟你还在手机上阅读梁实秋笔下的春节,关掉页面之后的下一条内容就是“姐夫小姨子把话说”,这便是我们在智能终端上阅读生态的日常。
让・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这样解释电视时代信息的配置:通过信息有条不紊的承接,强制性地造成了历史与社会新闻、事件与演出、消息与广告在符号层次上的等同。
而手机等智能终端同电视、广播一样,通过自身的技术逻辑实现了对世界和事件的剪辑:它实现了从黄晓明大婚和托尔斯泰的名著节选之间无痕迹的正常过渡,每一个用户的智能终端都是技术为个人进行系统剪辑和诠释的完整小世界。
电视将人们的感知世界塑造成一个可以任意显像、任意剪辑并可用画面解读的世界的思想(意识形态),而互联网的客户终端则大大地发展了这种文化帝国主义,它的剪辑和拼接比电视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加片段化、模糊化的图片和情绪化的判断,构成了一个更加不负责任的世界。
每当一个具有话题性的事件出现,相同或相似的图片和信息被各家网站、自媒体解读得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你在阅读这些根据情绪化的逻辑组织起的信息拼接前,即便了解它的不可靠性,但却无法拒绝它对你判断的影响;阅读少量文章后你得到了关于该事件片面、偏激的认识;阅读大量文章之后你的大脑又被它们搅成一团浆糊,随着事件热度的降低而不了了之,这时下一个热点事件又接踵而来。
你也许同时对伍尔夫的小说和范冰冰的八卦感兴趣,于是智能终端的个性推荐将伍尔夫的《到灯塔去》的片段,与范冰冰携男友李晨回家过年的新闻并置在一起,这种呈现方式看上去没什么奇怪,但它却在潜移默化地消解着经典之作的严肃性。
在印刷时代,经典是放在图书馆架子上的高头典册,越是经典的作品就拥有着越精美的装帧和越厚实的纸张,而现在它们与曾经口耳相传或者草草印刷的小道消息并置在一起。
印刷媒体时代,以文字为载体的经典不仅自身是传世之作,名家笔下的自然人文景观也因文本的经典化,而成为古迹供后世游览凭吊。崔颢登临的黄鹤楼、刘禹锡经过的乌衣巷、鲁迅幼时读书的三味书屋和其笔下人物孔乙己买酒的咸亨酒店游人如织,这些实体景观通过经典文章获得历史价值的同时,也反向加强了文本本身的经典化。
而这种传统的历史留存方式在现生了巨变。就中国本土而言,改革开放后的新景观塑造方式已经从文学经典变成了当红影视剧作。同样是江南水乡古镇,周庄在鲁迅的文学中获得不朽地位,而乌镇的走红则主要归因于黄磊和刘若英主演的电视剧――《似水年华》,“爸爸去哪儿”节目组曾驻扎过的营地,都成为了当地旅游业的新噱头,赵本山的小品让东北边陲的小镇铁岭,塑造成了全国闻名的“大城市”,即便是基于莫言小说的那片神秘的“高密东北乡”,其举世皆知的地位,也多来自于张艺谋电影《红高粱》而非诺奖。
如果说互联网智能终端普遍化之前,如《红高粱》般影响巨大的文学作品还有经典化的可能性,碎片化阅读成为主流阅读方式,则真正终结了泛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道路。
在鲍德里亚看来,大众传播将文化和知识排斥在外,它绝不可能让那些真正象征性或说教性的过程发生作用,因为那将会损害这一仪式意义所在的集体参与――这种参与只有通过一种礼拜仪式、一套被精心抽空了意义内容的符号形式编码,才能得以实现。
没有人有耐心在手机上理解逻辑衔接严密的文章,更没人认为在发掘精心构建的文学手法上值得花时间,网友需要情绪化的呐喊,越有煽动性的文字越能获得喝彩,挑动群体矛盾、顺应人性阴暗面的吐槽,最能得到广泛认可和转发,于是咪蒙等自媒体的佼佼者们才会苦心孤诣地去写《致》、《致low逼》等“10万+”,扯淡式说话和吐槽文字成为最受欢迎的文学形式。
也许这类文章会结集出版,但在时隔多年之后,除了反映这一历史时段人类思想的空虚和无聊之外,似乎并无甚存在意义。
人类在前互联网时代的历史中,均由文字作为主要的文明载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为不同的语言方式,比如先秦的散文、六朝的骈文、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每个时代创造的语言类型高度都令后世无法重复也难以企及。
在前互联网时代,一时有一时之文学,而碎片化阅读时代很难再造伟大的作品,文学表达本身(而非某种文学体裁)成为了遗产。经典化的文本将仅仅存在于过往已经完成经典化的作品之中,文字也再也无法形成新的旅游景点,如今造就奇观的重任,就落在了电影和综艺节目肩上。
这个时代严肃内容的呈现主要靠电影,当后世学者总结研究我们所处时代的经典之作时,电影会像唐诗宋词那样被看待和提及,它将成为被嗟叹凭吊的艺术形式。
对于文字地位的颠覆,互联网起到的作用远远大于电视和广播,电视和广播与文字是互斥的媒体形式,相互难以深入彼此腹地,电视分管图像,而文字依然存在于书籍报刊杂志等纸质出版物之中,铅字让文字在广电时代保持了本身的品相和尊严,记者、编辑和作家是受人尊敬的行业,如今“编辑”变成了“小编”,名称上的改变无疑体现着文字工作者地位无可救药的降低,想用一支健笔指点江山,横扫千军万马的时代不复在了,碎片化阅读时代的创作比的是“贱”。
而随着互联网作为一种“全媒体”式的呈现方式,尤其是如今碎片化阅读的主流――自媒体――的出现,让文章不再是字斟句酌,而是机械化的“码字”过程,绝大多数文章和网络小说,都是智力资源本身不占优势的文字生产者疲于奔命的产物,文字只会作为底层知识分子的谋生手段而存在,让这类文字经典化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现在早已不是文学的时代,20世纪的西方和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是文学最后的高光时刻。在扫盲和启蒙基本完成的现在,写作能力本身并不能称为一种特殊的技能而存在,教育程度达到一定水平的人都可以在自媒体上从事创作,各行各业人士均可以就自己深耕的领域发声,评论员作为一种职业很难逃避消失的命运。
在碎片化阅读时代,文字从业者(网络小说和记者、评论员、编辑)不再是引领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群体,更加优秀的毕业生投入到了技术机制的生产而非内容本身,文字不再凝聚社会大部分的智力资源,这必然导致文字生产水平的无限下滑。
碎片化阅读正在掀起一场强大的社会一体化进程,它席卷了文化领域,甚至是人类的精神领域,在文字继图像之后也被纳入到大众传媒竞赛的社会,整个社会组织都将建立在碎片化阅读和大多数用户阅读喜好的认可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