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消逝的记忆符号
时间:2022-02-17 09:37: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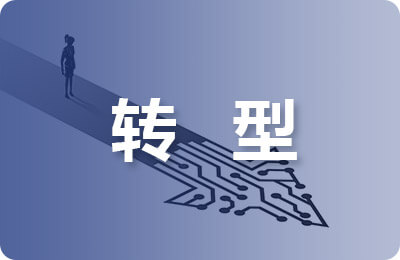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元年。大多数中国人第一次听说了“市场经济”这个词,第一次被鼓励去追逐财富,而且获得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具体目标。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机遇的变迁,强烈冲击着人们的固有思维。
30年,弹指一挥间。这中间有太多的符号,逐渐从我们的记忆中隐褪,有太多新事物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又消失,但归结起来,这30年间,中国社会这个陀螺,始终围绕着经济的圆心高速旋转,并实现了质的飞跃。互联网、WTO、柳传志、移动通讯、超女快男……成为这个时代的符号,但是,还有更多的符号也在这30年间逐渐变为历史,并且已成为人们记忆中的财富,渐渐变成了温馨的记忆片断。
时尚的收录机
1978年到1981年的这3年间,是整个中国社会开始发生转变的最初阶段,上海人的家庭生活场景也在逐渐发生变化。9寸、12寸黑白电视还没有大规模走进百姓家庭,因为当时买电视机不仅需要钞票,还必须具备另一种流通票证――电视机供货券。比电视机更早进入普通家庭的时髦电器,就是后来被人戏称为“饭盒子”的单喇叭录音机。
1981年在某些人的记忆中有一种特别的内容,因为在那一年的中国大地上,突然出现了两样最为时髦的景象:一是邓丽君缠绵、柔软的歌声,那种愁绪满腔、闻所未闻的悠扬旋律,几乎是在一夜间响彻了中国城乡的每个角落;二是当哪家的窗台上摆放下一台双喇叭收录机,简直就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情。
那一年11月,上海某兄弟二人凑钱想去买一台收录机。弟弟待业在家,白天骑上一辆破自行车全上海转,终于在当时的第十百货商店(即“”前的永安公司、现在的永安百货)探听到信息,说是第二天那里的五金交电柜台将出售飞跃牌的单喇叭卡式收录两用机,售价在180~200元之间(不需票证)。这个价钱哪怕是在今天都不算便宜,遂回家跟哥哥商量,兄弟俩凑了190元,弟弟第二天一大早骑上破车,7点多钟赶来商店门口排队,跟在长长的队伍后面等着买那台令人神往的收录机。快要轮到他时才发现,买一台那样的收录两用机需要200元,而此刻已经快轮到自己了,情急之下,他跟身旁的一位顾客借了10块钱,终于买到了收录机。然后,他把收录机押在那借钱人手里。让他在柜台边上稍等片刻,自己跑到隔壁弄堂,给正在工厂上班的哥哥打电话,叫哥哥快送10块钱来,也好赎回自己刚买到的收录机。但等他回到柜台边才发现,那个借给他10元钱的人,早已经溜之大吉了――人家花10块就买到一台价值200元的收录机,就跟白捡一样,还能不溜嘛!发现被人骗了,弟弟在商场大厅里当场大哭起来,疯了似地全商场楼上楼下找那个借钱人……等哥哥送钱来,发现弟弟被人骗了,安慰了好一会儿,才让抽泣不止的弟弟情绪安定下来。
就像有了一块巨大的心理阴影,这个被人骗去一台收录机的弟弟,从此以后,即使再紧俏的商品,宁愿得不到,他也决不会去排队购买。这件事情在他心灵上造成的影响,恐怕不仅仅是一台普通收录机那么简单。当时,许多上海人家渴求一台随时能够发出优美动听乐声的收录机,追求的不仅仅是时尚,而是被封闭数十年之后,所有中国人追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高度结合的具体表征。一台单喇叭收录机,以及它给中国人的生活所带来的冲击、影响和震撼,绝不是那么简单的!当时的社会购买能力有限,但依然阻挡不住城市百姓勒紧腰带,以极快速度接受更多的新生事物。
票证,第二种货币
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每家每户都有的那些五花八门的票证是第二种货币,其实一点都不为过。一市斤上海粮票可以卖到0.18到0.20元,一市斤全国粮票至少能卖到0.50元;每家每户一个月能分到3份香烟票(以旬为单位,每旬一份),每旬烟票大致可以买到的香烟是:5盒飞马、3盒大前门、1盒牡丹。一句烟票,如果到地下贸易市场去换,至少能换到12只鸡蛋或者3条半斤以上重量的野生河鲫鱼……至于自行车票、手表票、555牌台钟票,那就更能直接换来人民币,自行车票从60元到80元不等,手表票最高峰时卖到了90至100元……
粮票、油票、鱼票、自行车票、手表票、豆制品票、香烟票,甚至火柴票……据统计,从“”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止,老百姓每个月从街道办事处领来的各种票证,最多时达到40余种,范围几乎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针头线脑,无所不“票”。票证恐怕是人们对于过往时代的回忆里,最普遍、最深刻的记忆了。而在众多票证中,又以粮票与人们的生活最为息息相关。
那时,隔壁邻居家有谁在装卸公司当搬运工的话,那可实在是件让人眼馋的美差,老婆孩子,人前人后,也可以不无骄傲地向人炫耀“我家谁谁谁是做装卸工的!”弦外之音就是:我家不会有人饿肚子!因为那时一个装卸工每月粮食定量可以高达55斤;而一般知识分子定量只有29.5斤。粮票有着仅次于人民币的地位,印刷精美,票面上的计量单位细致入微,每种粮票能够购买何种粮食,也规定得清清楚楚。各地严格控制本地区的粮食供应,拒绝外地粮票在本地流通。“那时候的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农村流动到城市,小城市流动到大中城市,最大的束缚不是户籍,而是粮油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黄泽民回忆说。
1982年黄泽民到华师大工作,当时有个机会出差,参加在南京举办的一次学术交流。哪怕是邻近两地,粮票一样不能通用,只好凭单位介绍信去粮管所换全国粮票,也就是将上海市粮票换成“满天飞”――各地通行的全国粮票。手续十分麻烦,介绍信上必须写明出差的天数、出差目的地以及出差人的身份级别等等,数量也是根据介绍信上注明的事项,严格进行控制。
“票证实际上是计划经济一种非常具体的表现形式。当时供应短缺、资源有限,但计划经济条件下,价格固定不变,无法通过价格去调节资源的分配,因此,政府试图人为地制造一种社会公平公正,用票证这样一种分配手段,最低限度地来保证人民的生存。”黄泽民为当时的票证作了经济学上的注解。
1992年至1997年间,票证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时代的结束预示着中国由计划经济时的物资短缺时代,逐渐走向市场经济的过剩时代。
如今,悄然走进中国人生活的是一系列消费账单:水费、电费、煤气费、电话费、宽带费……从“票证时代”到“账单生活”的转变,折射出的正是中国几十年来社会结构深层次的变革。
全民皆谈“价格双轨制”
从1981年开始,国家允许企业在完成计划的前提下自销部分产品,其价格由市场决定。于是产生了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按国家规定价格统一调拨,企
业自行生产销售的产品价格根据市场所决定的双轨制。部分物价的渐进式放开导致了差价,形成了巨大的财富漏斗。简范舫就是90年代初靠价格双轨制起家的。
简范舫,那时只是一个在里弄生产组糊纸盒子的“工人”。1990年初,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与一位当时担任上海石化公司领导的亲戚商议,利用石化原料官价与市场价的巨大价格差,合作赚上一笔。他说服安徽合肥一家国有企业销售部经理,以每吨4000元的价格卖给他20吨石蜡,只比官价稍稍贵出200多元。接着,又以每吨5400元的价格与亲戚的企业结算。一趟下来,刨去开销,就净赚了2万余元。此后,简范舫又将进价每吨7100元的20吨聚乙烯,以每吨9000元的价格“转”到了上海一家乡办焦化厂。渐渐地,简范舫与一些贸易公司建立了联系,将生意范围扩大到浙江、河南等地的6家工厂。当时石化原料紧缺,不少化工厂都在为原料发愁,简范舫的“生意”越做越大,仅1990年下半年,净收人就有70多万元,1991年最多时一个月入账57万元,这在当时,简直就是一个神话。
类似于简范舫这样的情况,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尤其多。当初有外电报道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的短短数年间,中国俨然变成了一个大市场,城乡之间,人们口中吐露最多的,就是生意场的各种语言……全民经商的壮观场面着实令人叹为观止。现在,没有多少私营企业的老板愿意承认,自己当初就是靠国家的“价格双轨制”起的家,并捞得人生的第一桶金,虽然这已经是一个完全能够摆上台面的事实。
应该说,价格双轨制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一种特殊的价格管理制度。许多人认为,当初的价格双轨制是造成许多腐败现象的根源。在经济过热,供求矛盾尖锐、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高低悬殊的时候,一些政府部门或掌权的官员利用他们可以调拨物资的行政权力,占有计划物资,转到市场高价出售,从中渔利,即俗称的“官倒”。权钱交易让不少人从中渔利,大发其财。但同时,价格双轨开辟了在紧张经济环境里进行生产资料价格改革的道路,推动了价格形成机制的转换,把市场机制逐步引入了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生产与交换中,促进了主要工业生产资料生产的迅速发展。在经济体制转换时期,是实现中国价格模式转换的一种过渡形式。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不断完善,物价水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市场供求关系自我调节与上下浮动。虽然2007年高企的CPI使国家不得不在2008年初若干“限价令”,但这不过是临时的宏观干预,价格双轨制已经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
特殊商品下的“侨汇券”
2006年5月的《人物周刊》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忆及春雨》的文章,作者是音乐评论家贺国光,他回忆自己在1982年冬天给病危的母亲买药的故事。当时医生建议用一种叫血清白蛋白的进口针剂,但只有侨汇商店有卖,每一剂除了售价外,还需要30张侨汇券。但贺国光一家在国外没有亲友,身边的同事和朋友也多是普通老百姓,要想获得侨汇券的唯一办法,只有到黑市上去找票贩子(上海人俗称“打桩模子”),也就是人们俗称的“黄牛”。其间还颇有一番曲折:一开始“黄牛”疑心他是便衣警察,在贺国光说明母亲病危的原委,并拿出准备装血清蛋白的保温瓶后,这才相信了他。结果正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时候,却被民警逮了个正着。经过调查,派出所宣布处理决定:参与黑市证券买卖,人赃俱获,本应严肃处理,念其事出有因,尚属初犯,免于处罚,但赃款赃物必须予以没收。
侨汇券,乃计划经济时期一种特殊的票证,又称“侨汇物资供应证”或“侨汇商品供应券”。当时国内外汇资源紧缺,国内的一些侨眷收到海外亲戚朋友汇来的外汇,是没有办法通过邮局或银行直接领取的,而是须要持领款凭证,到银行按照官方当天的兑率,结算成人民币。同时,可以根据外汇金额,按照60%至70%的兑率,领取一定数额的侨汇券,凭着这种券证,可以到类似华侨商店、免税商店、友谊商店等指定商店买到当时市场上难得一见、普通商店根本没有的紧俏物品。那些像贺国光一样没有外汇来源,自然得不到侨汇券,却又急需去华侨商店买东西的人,就只能冒险去黑市,并花高价从票贩子手里买了。只不过,贺国光的故事最后有一个充满温情的结局:几天后,有人到单位门口找贺国光,竟是那个“黄牛”――他举起手里一只装着血清蛋白的保温瓶,说他那天在派出所看到贺国光掉泪时,他就已经想好了,要“帮帮你的忙”。
侨汇券于1959年发行,到1994年退出流通领域,历时整整35年。改革开放让国民告别了物资短缺的困境,中国人的口袋渐渐鼓胀了起来,商品种类也越来越丰富,普通市民再不用苦巴巴地羡慕那些手拿侨汇券、出入侨汇商店的人。在国家外汇储备逐渐充裕的大背景下,侨汇券的退出,也反映了政府外汇管理制度的具体变化。
比人民币更值钱的“外汇券”
王蒙在其小说《青狐》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有一次与一个老外另加外事翻译一起,去王府井一家商场的餐馆吃饭,青狐听到一个山东口音的青年问崂山矿泉水:‘这是么儿呀?多少钱一瓶?’她听到了服务员用不屑的京腔回答:‘那个,得外汇券!’‘外汇券’三个字像是提起了一个爪哇国的地名或是一种新式武器。偏偏那位山东哥们儿不大识趣,还继续问:‘么儿子叫外汇券啊?’服务员不再置理。山东哥们儿闹起来,提意见,抓住一个死理儿,矿泉水明明出在他们山东青岛,为什么不卖中国人,为什么不收中国钱……”
在一段时期内,外汇券和侨汇券并存。由于仅一字之差,许多人往往将其混为一谈。
事实上,外汇券虽然也属于一种流通货币的形式(全称叫“外汇兑换券”)。但是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经过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以另一种特殊的货币,用来替代外币在中国境内流通的人民币凭证,却是解放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由于外汇券与人民币的比价为1:1,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境外人士到中国可用外币兑换外汇券,应付日常开支,当然也受到了另一种“礼遇”。此外。持外汇券还可以到特殊地点如友谊商店、侨汇商店等,购买当时人民币无法购买的紧缺商品。
发行外汇券的目的是加强对外汇的管理,禁止外汇在我国国内市场上流通。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还不稳定,为了避免大量外资涌人破坏中国经济秩序,外汇券应运而生。但外汇券的存在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人民币与外汇券平行流通,使人们通过各种办法用人民币换取外汇券,外汇券黑市价猛涨,与人民币实际上并不等值。
由于外汇券实际上是当时国内特定环境下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的货币,与我国单一的货币制度不符,中央银行在
1993年底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中做出决定,外汇券从1994年1月1日起停止发行,1995年1月1日正式停止流通。
疯狂的股票认购证
股票认购证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初期,发行新股时出现供不应求的问题时,采用的主要方式之一。
洪彦龙当时正在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现在的东华大学)读研究生,常听人说到1992年上海人买认购证发财的故事。1993年“赣江铃”(现在叫江铃汽车)发行的时候,他受几个同学的鼓动,拿出了手头仅有的2000元。当时20多个人共凑了七、八十万,委托两个人坐飞机到南昌去购买。摇号结果公布,洪彦龙中了两个签。高兴之余,却发现问题也来了,“赣江铃”原始股的发行价是3.60元,但他却没那么多钱去认购股票。正好有同学感兴趣,就以每张1700元的价格,从洪彦龙手中把两张中签表买走了。虽然洪彦龙误打误撞地从认购证上赚了1400元,但他算了笔账:“赣江铃”上市第一天的收盘价是8.80。也就是说,如果当时有钱买下股票,即使是在当天就抛出的话,那么,这天他就可以挣到8400元。
老证券人应健中回忆说,认购证的出现,实际上是人民银行面对当时证券市场逐渐升温发热的态势,不得已而出台的一个解决方案:先发股票认购证,凭认购证摇号认购股票。
持证须知第二条写着:“本证收取购证费30元整。除去少量的工本费、销售费外,绝大部分捐赠社会福利机构。无论中号与否,购证费概不退还。”就因为这么一句简短的说明文字,使许多人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究竟该不该买,认购证发行时一度沦落到银行和邮局门口摆地摊、国有企事业单位动员摊派的地步。
然而,就在1992年的认购证全部销完之后,由于股份制改造提速,原定股票发行额度大大增加,于是发行结束后不到两个月,认购证的黑市价就已被炒得相当火爆。从每10份连号1万多元,到每张1万元以上,对那些最终依靠股票认购证改变了自己命运的人来说,认购证是一张通向新生活的通行证;而那些与之擦肩而过的人,则追悔莫及。
1994年,证监会取消了股票认购证制度,新股认购开始实行上网定价全国发行。
曾经不起眼的“纸分币”
一家专业钱币公司的纸分币柜台前,站着一位执着的买家:“有货随时联系我。如果碰到退货的话,我愿意出高价买。”从2007年开始,纸分币收藏迅速升温,在钱币市场严重缺货的情况下,买家们甚至愿意出高价购买或到外地市场寻宝。其中,长号5分币由于存世量少,其市场价值已较其面值上涨了7999倍,高达400元。
纸分币收藏的牛市始于2007年4月,第二套人民币纸分币正式停止流通。据了解,第二套人民币是我国各套人民币中唯一发行了纸分币的一套。这也就意味着现行通货中已经再无法见到纸分币的身影。相比之下,铝制硬分币在全国各地的存世量还较大,但实际上也已渐渐淡出流通领域,在城市中的应用更是少之又少。
曾几何时,作为一种辅币,分币的流通量是非常大的。1分钱能买一杯茶,3分钱能买一块豆腐或一支冰棒,4分钱能买一块烧饼,9分钱可以买盐买醋买酱油,16分钱能买一斤米,65分钱能买一斤肉……而今,商场的货柜上,连几角钱的标价都已经难得一见;偶尔在超市里还能遇上几分钱的零头,但大多是会被四舍五人的。
100元的大面额钱币面市时,曾有经济学家说是物价飞涨的佐证,也是货物贬值的佐证。但无论如何,人们一面撇不去对分币的怀念,一面却早已习惯速发展的经济生活带来的物质享受。恐怕以后,也只能从收藏市场看到那些花花绿绿的纸分币,或是用数十张纸分币叠成一个纸菠萝、纸帆船一类的玩具,以示纪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