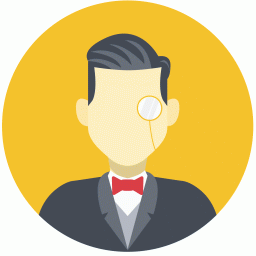日常、内心与现实的三重变奏
时间:2022-10-25 07:42:14
摘 要:晴朗李寒是70后诗人群中的佼佼者,近些年获得过“闻一多诗歌奖”、“赤子诗歌奖”等奖项,其写作风格也渐趋稳健超拔而独树一帜。诗人的写作立足于日常生活,与此同时,内心也充满着中年的迷津,但并不放缓追寻的脚步。在面对现实的灰暗时,他主动以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担当精神“介入”与关怀现实,在不断地探索中,将写作延伸至更高远的精神境界。
关键词:晴朗李寒;诗歌;常态写作;迷津与超越;介入现实
中图分类号:G609 文献标识码:A
如果对70后先锋诗人群落做一个整体扫描,很容易发现,晴朗李寒是他们之中很特殊的一位。这种特殊源于他对诗歌的虔诚与敬畏,正如诗人自己所说:“我一直相信诗歌的力量,相信文字背后的神秘力量”。这种“相信”成为了诗人二十多年来对诗歌写作坚持不懈的动力。对晴朗李寒而言,这种对生命的热爱,对诗歌的信仰或许已成为一种宗教。生活――生命――诗歌这三种元素相互渗透、相互融汇,构建起了诗人的诗学体系。
一、立足生活的常态写作
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先锋浪潮中,李寒是一位时代的“迟来者”,他的诗歌写作与“狂飙式”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既不遵从某种理论的既定套路,也不追新逐奇引领潮流,而是始终顺从着自我的情感直觉与语言习惯,保持着不紧不慢的步调,不盲从,不张扬。与其说李寒的诗是一种创造,倒不如说是一种还原。他将诗歌还原为生活,使生活恢复诗意,让汉语恢复灵气。在写作中,他对五花八门的形式实验保持着应有的警惕。尊崇“回归生活”与“回归自我”的写作宗旨,维护着诗歌的常态精神。
在我的诗中看不到电闪雷鸣、黄钟大吕的东西,因为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平凡、平静、平常。一天一天,上班下班,路过那些相同的事物,看着那些面孔相似的路人,做着几乎大同小异的事情,我唯一的爱好,便是在这些事物中发现小小的不同,找出细微的差别,就像女儿从图书中找出两组相近图案的不同之处一样快乐。
――《活着,写着,爱着……》
从这段诗歌自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常态在李寒的诗歌写作中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构成了诗人理解世界的方式:无论是诗歌还是生活,乃至生命,其最基本的原始存在便是一种平常自在的状态,而“先锋”不过是其中偶尔“凸起”的部分。在李寒看来,“诗并不飞翔,凌越大地之上以逃避大地的羁绊,盘旋其上。正是诗,首次将诗人带回大地,使人属于这大地,并因此使他安居。”发现与坚守日常才是诗歌创作的核心。李寒大都以平凡的生活入诗,在“日常叙事中发现诗的本源”。
在对诗歌的题材与内容的把握上,李寒从不夸饰,而是以一颗赤子之心,表现出对常态生活的真诚与尊重。从诗歌的命名,诸如《爱情》、《轮回》、《午夜》、《阵雨》、《小区生活》、《高速公路上》等等,就不难看出,李寒的创作涉及了广博的生活内容。在他的诗歌世界里,平淡无聊的生活往往变得亲切温暖、生动活泼、多姿多彩。无论是在《爱她的……》、《你的身体》里对妻子炽热的爱恋,还是在《时光窃贼》中对“窃贼”这一形象的生动刻写,李寒都是将自己的镜头对准生活的细微处,用敏锐的嗅觉发掘日常中被忽视的诗意,用自然的笔法描绘着原汁原味的生活状态,充分显示出了诗人发现生活的能力。
情感的自然与率真,是李寒常态写作中的另一大亮点。在冷抒情泛滥或者拒绝抒情的先锋潮流中,诗歌已无法真正表现人们复杂的情感世界。从这种意义上讲,我更愿意把李寒当做一位抒情诗人。他的诗歌敢爱敢恨,敢于将自己的情绪和感觉倾泻于笔端。该悲伤的时候便悲伤,该大声说爱的时候便说爱,该愤怒的时候便拍案而起。可以说,诗人的每一首诗都是性情之作,是心灵的本色出演,不矫饰,不虚情假意。
我厌倦了光滑和细腻,厌倦了精致和完美。/我爱上了单一的事物,/和它们粗糙的部分,/我爱上了残缺,没有结局的故事,/爱上了棉布,拙劣的黑陶,露出草梗的纸。//我厌倦了繁复,重叠,厌倦了涂满油彩的/面孔,和多变的表情。/我爱上了缓慢的旅程,爱上了中途的阻隔,/而不是瞬间的抵达。我爱上了等待,/等待中的焦灼。……
――《我爱上了……》
一首《我爱上了……》真切地道出了诗人的爱与憎,能够将自己喜爱的事物与厌倦的事物细腻而准确地呈现出来,既依赖于诗人的观察力与感受力,更需要诗人由心而生的感情。这种“想爱就大声说出来”的写法其实是在呼唤一种诗歌情感的自由。在抒情诗日渐式微的时代,李寒渴望一种回归,渴望回归到情感充沛、真挚的诗歌语境中来。
博尔赫斯曾说:“一个人写诗是受激情催迫的,更确切地说,他必须宣泄他的激情,因为如果某个主题追着他写,非让他写不可,使他不能安宁的话,那么他就得写以便摆脱它……”李寒也是属于这类“情绪主导型”诗人,诸如《雨说下就下了》中那种“青春期式”的忧伤;《多么美好的一日》中对美好时光的赞叹;《愤怒之诗》中对社会弊端的痛斥等等,这些诗篇大多是强烈的主观情绪“催促”着诗人去抒写,这种感情推动表达的方法,有别于“理念”或者“主题”先行,剔除了矫揉造作的因素,保留了一份可贵的纯真。与此同时,诗人的这种写作方式,并非发泄自我以获得宣泄的,而是在情感的正常释放的基础上注重诗意的提升。
诗人有许多写给妻子和女儿的诗篇。这些都可以当做情诗来读,其间流露出的感情真切而深厚,细细咀嚼令人感动不已,李寒丰富的情感世界直接作用于诗歌,使之洋溢着“爱”的暖意,这种爱是诗人珍爱生活的情感基调,也是使世界“软下来”、“慢下来”的一种方式。总的来说,无论是情绪推动下的抒怀,还是“爱”的诚挚表达,都是常态情感的具体体现,而情感的常态与真实正是李寒诗歌的核心所在,我们由他的诗看到了抒情的深度。
李寒诗歌的常态抒写,还体现在对诗歌语言的运用上。语言是诗歌的灵魂,当各种语言实验风行诗坛的时候,诗歌开始被语言所奴役,我们对诗歌语言的“魔力”与“诗性”的兴趣似乎在逐渐衰减,汉语诗性的断裂则成为了当下诗歌的主要病灶之一。而李寒是那种坚持让语言保持鲜活气息的诗人,在他的诗中很少有华丽的辞藻,也缺少技术性的坚硬语质,而是处处闪耀着有韧度、有温度的智性语言。
然而不管是选择爱,还是选择哲学探险来追寻心灵的超越,其实诗人一直都未曾获得真正的解脱。他总是在诗歌理想的道路上跋涉,在这荆棘丛生的途中,有一种不可复制且无法消除的“来自灵魂的深处的疼痛感”一直伴随着诗人。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生命的痛苦,诗人在窥探生命意义的同时也萌生了这种强烈的灵魂刺痛感,在接近真理的同时也接近了深渊,随着他诗歌写作的进一步深入,这疼痛也必将会越来越强烈。在某种意义上讲,过度强烈的心灵刺痛必然会诱发心理的矛盾与分裂。许多优秀的诗人都具有精神分裂的倾向,他们的精神感知与肉体存在出现了某种落差而不能得到平复,从而陷入了精神分裂的境地。李寒的很多诗歌中也表现出灵肉分离的状况,他曾多次写道,希望在自己体内发动一次革命,将身体杀死以得到精神的解放与自由,但他把握住了分裂的“度”,在走向精神悬崖的同时,他能将自己拉回到现实中来,这份理性与智慧是很难得的。
李寒的诗歌充分显示出“心灵化”的诗学特质,他向我们展示了复杂的精神世界。坚持独立写作的诗人一直保持着 “倔强”的姿态,这不仅体现在与现实的关系上,也体现在与自我的关系上。他不断地在内部与自我抗争、妥协、再抗争,在这种轮回的进程中,每一次的自否都是一次超越,它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艰苦历程,在这种特殊的体验中,诗人通过诗歌完成了对自我的重塑,与此同时也真正体证了生命。
三、面对现实的良知“介入”
诗歌力量的彰显来源于诗人内心不竭的追求,诗歌的深度也来源于诗人心灵的高度。纵观李寒的创作历程可以发现,他是一位逐渐成长的诗人,他既专注于日常书写也在寻求灵魂的超越与诗歌境界的提升。诗人在关注自我、审视自我的同时从没忘记对现实社会的关注,用诗歌去触摸埋藏在时代泡沫之下的社会底色,从而完成“大我”的书写。事实上,这种“大我”从未完成过,而是一直处于无限的接近之中。
晴朗李寒自己曾说:“诗人更要能听到矿井之下尸骨的呐喊,豆腐渣废墟下孩子的,凶猛的挖掘机履带碾轧下拆迁户绝望的哭嚎。如果对社会问题麻木不仁,你就不配做诗人”。在他看来,诗人应该保持对时代的警惕审视,对文化的批判精神,对当下现实的关注,对生命的悲悯。这才是诗人应该有的责任与担当。
一个日常的女人,被岁月打磨得面目模糊。/如今,她站在菜市场里,/为晚餐是土豆白菜,还是萝卜蘑菇,而迟疑不决。/她的自行车粘染了尘土和泥泞,/车筐有些变形,(它一直装载着一家人的食粮)/她要趁着昏暗的天光,挑选那些喷过水的蔬菜,/要为称的高低与小贩较量。/“菜还是这么贵,天都暖和了。”/“便宜不了的,什么都长价!”菜贩厌烦了她的挑拣。/“孩子正在生长,再买些苹果吧。”10块钱6斤,尽管觉得贵了,/她仍然仔细地挑了些。/“他累了,爱喝口小酒,就着我炒的花生米。”/土豆两块,胡萝卜一块五,西红柿一块八,苹果五块,花生米三块,/红的,绿的,慢慢挤满了车筐。/一个清贫的女人,熟练地掌握了生活的算术,/她清楚,如何让每月的600块钱,正好与下月衔接。//这是普通的一天,三月八日,/我见到一个普通女人,从菜市场缓缓走出,/她笨重的身体,隆起的腹部,/很快便会被黑暗和汹涌的车流淹没。/而在她的子宫深处,/那个一无所知的小小胎儿正在吞吐着羊水,/用脐带吸吮着养分,/一天天长大。
――《中国母亲》
诗人擅长叙事,在不紧不慢的叙事节奏中,一位中国女人日常生活的画面向我们缓缓展开,买菜细节一览无余,这中间包含着女人的面容、语言、动作、神态等细节的精准呈现。诗人通过还原的方法将我们带到普通人的生活现场。诗中的“女人”是千万中国女人的缩影,也隐喻着我们的祖国母亲。但很显然,诗人的情绪在叙事中遭遇了“泄密”,他对“中国女人”的怜悯与同情是不言自明的。我们能感受到诗人在面对“女人”时心中的酸楚与疼痛。这样的情感不同于“五四”那群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而是设身处地站在“底层”的位置述说着他们的遭际。这样的“介入”与悲悯姿态是难得的,它抛弃了高高在上的遥不可及,多了一份贴近人心的冷暖相知,用平等的心来感知他们的辛酸,给予最平易近人的抚慰。
对于社会苦难,李寒一直保持着怜悯之心。《冷风景》中的红薯小贩、流浪汉和卖艺夫妇,《换歌》中的无辜逝者都成为诗人的书写对象。在诗中,李寒向我们展示着社会底层的真实面孔,为了唤起我们被搁置的善良而奔走呼号。除此之外,重大的社会事件也没有逃脱过诗人的眼球,诗人竭力从动车追尾事件、卡扎菲之死等公共事件中询问背后的真相,对地震等灾难表现出的哀痛,都体现出了诗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笔者认为,作家思想观念或者写作态度的转向与时代状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09年以后的李寒在诗歌中多了些“愤怒”的情绪和“介入”的姿态,这与体制、时代风貌的改变不无相关。社会风气的退化,让宽容的诗人再也无法抑制自己心中的悲愤之情,他便选择对社会不公以最严厉的斥责,对社会丑恶予以最决绝的回应。而诗人的不满则是经过理智的过滤而流泻出来的铿锵之词。
谁还记得瘦弱的青春?/广场,马蹄,被压制的下体,/口号,铁拳,被败坏的初恋。//激情之血渐渐退潮,/没必要焦虑,不至于绝望。/只是愤怒得还不够,/反对得还有些浅。//秋天近了,革命还远,/四十岁的人,想重新做回青年。
――《敌意之诗》
诗人对社会弊端的揭露从来不留情面,他敢于大胆“掀翻酒徒们盛宴狂欢的桌子”(《帝国黄昏》),除了遵循心中道德与良心的准绳外,他无所畏惧。作为译者的李寒,长期从事二十世纪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歌翻译工作,不免在精神血脉上与阿赫玛托娃们气息相通。面对社会丑恶与体制挤压,他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拒绝趋炎附势。他审视、诘问、质疑时代的同时却从不绝望,字里行间里流露出“鲁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以“与你们不同的方式”(《我要这样爱她》)深爱着祖国,在骨子里亦坚信“那些卑鄙的灵魂/会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挽歌》)而当这些声嘶力竭的呼喊无法改变不断陷落的现实时,诗人则表现出特有的孤高与骄傲――“他们不配/放逐/一个高傲的诗人/一个腐朽的帝国的掘墓者”,这是诗人在以最后的尊严向无奈的现实发起挑战,这份勇气与担当如一把利剑,直指时代的痛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