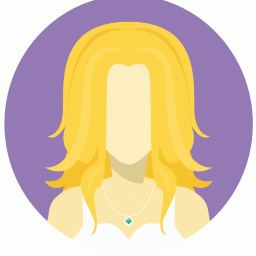名人传记的法律道德之问
时间:2022-10-11 10:52:04

唐葆祥(上海昆剧团一级编剧):
言慧珠我没接触过,所以对言慧珠我没有多少发言权。俞老我们在昆剧团的时候,从1978年开始一直到他1993年逝世,我们都在一起。而且他委托我给他写了一个传。这个是90年代的事情了,已经过了十几年了。最近看了言清卿的《粉墨人生》后,大吃一惊。该书对俞振飞的贬低和污蔑,越过了真善美的底线。在我看来,真善美是一切人类活动的最高目标和终极指向,也是文艺批评中检验作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美学标准,名人传记也必须得到真善美的检验。真,是指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传主的生活本质、历史贡献;善,是指作品的倾向性,指作者在什么立场用什么视角来评判传主;美,是指艺术手段、文字风格等艺术形式如何与内容和谐地统一。真善美当中,真是最主要的,是前提,如果一个作品,内容是虚假的,那么善与美都无从谈起。一般来说,我们为某一个人立传,那个人一定有可立之处,一定在某个领域有突出贡献,或者对某一个历史阶段起了推动作用。我们写传记的目的,就是要突出传主的历史功绩和他的人生亮点,供后人以启发和借鉴。所以传记必须以真实为前提,容不得虚构与戏说。当然,历史人物是复杂的,他们有功也可能有过,他们的性格即便坚强刚毅,也可能有软弱的一面。他们的思想崇高伟大,也可能有卑微的瞬间。我们的传记作者如何客观真实地描述出这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呢?我们对于一些似是而非道听途说的资料如何来甄别呢?这个完全取决于作者的立场和态度。就拿俞振飞来说,他是社会公认的京昆艺术大师,我们大多数人都想知道俞振飞取得了哪些卓越的历史成就,以及这些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但是有的人不是这样,他们是借写传记之名行泄私愤之实。比如言清卿口述的那个《粉墨人生》,其中每章每节都充斥着对俞振飞的谩骂和诽谤。言清卿是言慧珠与谢郝维的儿子,他与俞振飞原本没有感情基础。言慧珠在中被逼自杀的时候,他在实验室,他也受到了社会的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他把满腹怨恨错误地向他的继父俞振飞发泄,在这样的情绪支配下,他是不可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出这一段历史的真实面貌。比如,他在书中把猜测当事实――他把一个连俞振飞是死还是活都弄不清楚的患病老人的话当成依据;他把言慧珠被迫害致死归罪于俞振飞见死不救、推波助澜;他还借他人之口谩骂诽谤俞振飞……我觉得这就越出了道德的范畴,而是触犯了法律,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让人最不能理解的是执笔者,他在文章、结构和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俞振飞的仇恨,他在章节的题目上,选用了耸人听闻的字句。按理说执笔者与俞振飞既无交往更无过节,为何如此恶狠狠呢?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言清卿自己在无意中透露的一个情节让我有所领悟:这本书一共印25000册,如果售完,版税达8万,他与执笔者各得4万。原来有如此的利益驱动!无独有偶,日前在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有一本叫做《明清文人那些事》的书,颠覆了名人形象:书中揭露了郑板桥是个同性恋,而李煜是“潜规则”的发明人。其实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就拿李煜来说,他家里养了一个戏班子,自己既当编剧导演又当教练,他培养出来的15位女演员都是他的小妾,这个在他的《一家言》这本书里都有明明白白的记载,这种情况在当时社会制度下是没有什么稀奇的。现在有人把这些事挖掘出来,又与今天的潜规则挂钩,这样就可以吸引眼球,制造卖点。原来,颠覆名人形象,不仅成为一种时尚,而且背后还隐藏着巨大的商业利益,为一己私利不惜谩骂攻击甚至造谣毁谤,颠覆名人形象。这不只是一个狗仔队的做法,简直是。
蔡正仁(著名表演艺术家):
我觉得名人传记有一条,至少要建筑在以事实为基础的前提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俞振飞是当今昆曲泰斗,他的弟子遍布全国,也遍布海外,影响非常大。《粉墨人生》里讲到很多俞振飞所谓“人家不知道的事情”,牵涉到大师的品质问题,这个问题就不是一般性的问题了。我当时看到这书的时候,一边看一边怒火在上升。我很少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真的才刚刚感觉到,人世间怎么会有这样的中伤,怎么能这样恶毒地攻击一个去世那么长时间的老人!作者凭自己的一些想象,或者道听途说,当然也有一些所谓的事出有因,但很多都是不对的。比如说是俞振飞追言慧珠,还是言慧珠追俞振飞,这些事,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他居然会那样写。我就真的非常不理解,这个人到底要干什么?难道他不懂得,那么多牵涉到俞振飞的事实,需不需要去了解一下?那么多了解俞振飞的人都健在,为何不去了解一下呢?他都没有做。而且书中把一些“重要的问题”还用黑体字把它拎出来,这个是我愤怒到极点的原因,道德居然沦丧到这种地步!这本书还有一点非常恶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知道了,他“引用”张三讲什么,李四讲什么,但你仔细一看,张三已经不在了,李四也已经不在了,死无对证。这就很具欺骗性。包括我的夫人,跟俞老非常熟的,她看了这本书以后也大吃一惊,说俞老师怎么是这样一个人?蒙蔽性、欺骗性很厉害。有些事情是事出有因,但是给他这一写,完全变了味。把一个非常有修养、艺术成就的艺术大师,描绘成像恶魔一样。稍有一点良知的人能允许这么做吗?我们不能置之不理,要维权,要对这样的老艺术家保护。出这样的一本书,是不是触犯法律我还说不清,至少我觉得道德两个字问题是很大的。
沈鸿鑫(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名人传记跟小说、戏剧是不一样的,它的主要特征就是真实性。所以我认为真实性是名人传记的灵魂。传记基本上不允许虚构,描绘的人物、主要的事件情节都要有事实根据,不但要求时代的真实、生活的真实,还要有时间条件和社会条件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不要说名人传记,就是一些历史剧,比如大家都知道的《桃花扇》,这个戏在写的时候就有一条原则,所有的事件都是有根据的。孔尚任为了写《桃花扇》,读了大量的史书,做了多方面的采访和详尽细致的考据。《桃花扇》里有29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在历史上都是确有其人。就是像李香君,也是有根据的。所以我是这样认为的:纪实性文学跟虚构为主的文学创作应该区别开来,小说可以虚构,可以典型性,可以“拼凑”,但是名人传记必须历史上确有其人,不能张冠李戴,也不能无中生有。传记的真实性让读者产生一种极强的可信赖度,由此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染力,这种感染力是一般虚构的文学所不存在的。现在有些传记作品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我们的文化正在娱乐化,传记也受到娱乐化的影响。很多东西在戏说,但传记不能戏说。现在为了传记的戏说已经引起了很多官司,比如说《霍元甲》电视剧,里面增添了很多男女爱情方面的故事,这个东西是霍元甲所没有的,结果引起了霍元甲后人的不满和抗议。还比如电影《梅兰芳》,又发现了很多不符合史实的东西,比如跟齐如山的关系,他里面写齐如山,写他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要求梅兰芳为日本人演出,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违反事实的。梅兰芳1932年就到了上海,跟齐如山分开了,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联系,要到1947、1948年的时候,齐如山到台湾去,取道于上海,这个时候才跟梅兰芳见面,所以齐如山要梅兰芳为日本人演出,这个都是子虚乌有的东西。后来齐如山的后人就提出了,要求封掉这个电影,不许这个电影放映。这个东西都是不尊重史实,任意地虚构,造成了官司。还有一个就是隐私问题,有些人凡是隐私的东西都很感兴趣,喜欢把它无中生有地扩大、放大。传记作者和媒体不应该去迎合这种东西,现在我们确实是在迎合这个东西。我觉得一个传记作家应该非常严肃地对待传主的隐私,不要为了迎合需要,丧失传记的严肃性和真实性。
费三金(上海戏剧学院戏曲理论研究室教授, 一级演员):
我写了一本《言慧珠传》,当时学校让我写《言慧珠传》的时候,我考虑了两三个月才把任务接下来,为什么呢?我一再思考,到底从哪个角度写?我记得戴厚英小说中有这么两句话:“批判会上无好话,追悼会上无坏话”,有些人写传记,把传主“好”的扩大,或者把“坏”的扩大。你说他“好”的不真实吗?或者“坏”的不真实吗?是真实的。但是只写一面,又是不真实的人生。现在要我要写一个活生生的言慧珠,既写她艺术上的成就,又写她的人格缺陷。这个度该怎么把握?所以我考虑了两三个月,才跟出版社的编辑见面。现在很多出版单位嘴上在讲社会效益第一,肚子里恐怕都是经济利益第一的。当然情有可原,但是得有底线。他们曾给我提出过一个要求,我拒绝了,我说,如果你们要考虑这本书成为畅销书的话,可以请香港的狗仔队来写,言慧珠可以写成艳照门。这样的书你们敢出吗?反正我不敢写。我还是决定写一个艺术家的言慧珠,但是在写“艺术家的言慧珠”的时候,我不回避她的性格缺陷。我把她的性格缺陷和人生上的失误放在三个条件上写:一个就是她所生存的社会大环境,一个就是她的家庭背景,还有就是她个人的处境。我觉得写传记文学这点很重要。当人类对这个世界有认识的要求,他反映在艺术上,就是现实主义。当人类对这个世界有改造的愿望,反映到艺术上,会产生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可是传记文学绝对不能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传记文学必定是现实主义的一个大的支流。我在写传记时,两点最难写,一个是言慧珠的私生活,另一个是言慧珠跟俞振飞的婚姻,这一段啼笑姻缘,不知道怎么写。你把内情全抖露出来,又牵涉到言慧珠的隐私;不谈,他们在舞台上的合作,确实在50年代,从北京到上海,达到了艺术的高峰,又回避不了这段历史。写传记要写真实,这个毫无疑义,可是写真实不等于写隐私,虽然隐私也是真实的。我把什么都暴露了,就是写真实了吗?这里又牵涉到现实主义不可能没有作者的倾向性,但是倾向性必须压到最低最低。你把这些东西全写出来,你觉得社会效果会怎样?我要写的是为一个艺术家立传,是要给后人留下一笔精神财富。但是有些传记,给后人留下的是精神垃圾。本来两年前接到写《言慧珠传》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但是没想到,一本书即将完成的时候,帮助了我认识这些问题。
刘言浩(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我是法院的,我自己也办过一些名人官司。关于名人传记,一般涉及到三种权利:人格权、隐私权、名誉权。所谓隐私,就是没有公开过的、本人也不愿意给别人知道的事情。你如果公开之后,导致其社会评价降低了,就牵涉到名誉权的侵害问题。上海法院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处理过一系列有代表性的名人名誉权案件,像早期的徐良名誉权侵权案,还有静安法院审理的范志毅案件,还有一中院审理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喜儿扮演者茅惠芳的案件,还有著名作家余秋雨,香港著名导演唐季礼,以及最近大家都知道的谢晋的这个案件。上海法院这20年来,已经有了一套相对比较成熟的处理办法和规则。像名誉权、隐私权主要适用的法律有《宪法》、《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最严重的可能涉及到《刑法》。《民法》对于名誉权、隐私权的规定都很简单,到底怎么保护,需要法院在实践中去总结。我们处理这类案件关键是判断两个问题。第一是隐私权,如果你是一般老百姓,没有任何知名度,那么你只要不愿意披露隐私,别人披露了你就可以告他侵害名誉权,并且一定能够胜诉。名人的隐私权相对少一些。第二是名誉权,你只要说了我的事情,导致我社会评价降低,法院就要支持原告的请求。这一点主要针对公众人物。怎么判断公众人物?公众人物有历史人物,有健在的人物。相对来讲,对历史人物的保护范围可能要窄一点,大家研究他评价他的空间要大一点。对于健在的公众人物,要看什么公众人物,比如像政治名人,因为他是借助公权力出名的,社会大众就可以对他行使不受限制的监督权利。像文化名人、娱乐名人、体育名人,他们的名誉权保护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提出限制性条件:就是你报道的,必须是社会公众利益需要关心的内容,不能无限制报道,对于纯粹是私生活的事情就要有所控制。像一些著名的导演、演员、艺术家,你可以报道和表演艺术相关的,但是他的私生活,比如第三者插足这些事情,跟他的表演艺术无关,不能够随便报道。
张伟品(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法律是我们的社会准则,社会准则的门槛就应该定在私人行为向社会行为过渡的那根线上,定下来。所以我认为很简单,我们应该建立行业规范,建立出版规范。比如说在行业出版规划上取消“传记文学”。注意:不是取消其实质,而是取消这个名词。“传记文学”把一个概念搞得很模糊,传记是传记,文学是文学,把真实和虚构搞到一起,容易造成混乱。分开来后,如果你写创作的传记,那就不能出版。我们习惯上把“文学”跟“创作”联系在一起,一说到文学就想到创作,一说到艺术也想到创作。今天我手机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有一部新的电影开拍了,电影的名字叫做《孔子春秋》,又是一部关于孔子的电影,其中导演阐述这部电影的时候说,我们这部电影完全按照史实,严格按照历史上的孔子的事件一个一个拍下来,完整地反映。但最后来了一句:为了达到好看的目的,我们为孔子设置了两个情敌――你看看,一个人的逻辑可以混乱到如此程度!所以我们应该有真正的行业规范。前面一句话是“史实”,后面一句话是“两个情人”,这个不可以的。说一句大不敬的话,有些作家已经把自己降低到了的程度。是什么呢?出卖你的智力劳动去换钱,他不对文字本身负责。我们法律上规定要文责自负,但是他又不负责,他只是卖钱,其实是个,文字。还有一种,像我们今天讨论的这本书的例子,是一个合作的形式:有一个人口述,一个人执笔。这种形式尤其在艺术界非常流行,因为很多老演员、艺术家在文字上确实存在一定困难,需要一些文化工作者去帮他们。到底这两个作者之间各自如何承担责任?法律责任怎么界定?著作权怎么定义?这倒是需要我们在法律上作出明确界定的。执笔者说,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写,那个主要责任由他负,我完全不负责任,文责我不负的。我们的法律上,著作权方面是否还存在一些类似的空白。这些方面,我们是要加点力气的。
朱文华(复旦大学教授):
我主要是搞传记理论研究的,我们不妨从《粉墨人生》说开去,谈及一些相关话题。从传记理论上讲,任何传记作品实际上应该是一种史学文本,它的主体内容应该是对一个特定的历史人物所经历过的一段特定的社会历史生活场景的客观描述,因此传记写作实际上是写历史,这就必须遵循史学著作写作所应遵循的一般原则和方法,就是作者要做到凭证据讲话,实事求是地反映、描述、介绍历史人物的基本情况,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功与过、对与错都要如实写出,不要忌讳不要回避,同时也不要做过分的吹捧,总之在传记写作当中不应当有什么虚构,加入想当然的东西。合理地想象、推测,这是小说家可以采用的技术手法,传记作家应当远离这一点。一个严肃的传记作家,应当把自己定位于历史学家的角色,因为写传记要为历史负责,为历史人物负责,为历史人物的家属负责,也为自己负责。不过我感到需要注意的是,在具体写作当中,要分清传记内容的主次和描述角度,相关的评论性的意见要尽可能做到客观公正,不感情用事,不迎合某种媚俗的倾向。一般地讲,最好不要把传记有关私生活内容的场景作为重点来描写,如果你需要一些细节来反映传主的性格个性等,点到为止就可以了,不要做过分的渲染。你写一部传记过多地关注传主的所谓私生活,可能恰恰反映出传记作者本身的道德情趣不太高。另外,对某些名人的遗属在有些问题上纠缠的情况,我谈我个人的看法。传记作者为某一个传主写传记,并不是代表组织上为某一个死去的人写悼词,这是个人的文化行为,不必过于迁就传主家属种种的期待性要求。对于传主的家属,从理论上说,只要传记的思想倾向没有出格的地方,传主的有关情况没有严重失实,似应该予以理解和配合。退一步说,局部细节偶有失实之处,传主的家属也要表示宽宏,主要要看作者的整体性态度:究竟属于别有用心、居心叵测的诬蔑诽谤,还是属于写作手法上的技术性问题。如果是前者,当然可以去告他,你有的权利。如果仅仅是技术方面的原因,最好你能宽宏大量地友善地和作者交换意见和看法,争取以后再版时做某种修改。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激化矛盾,才有利于造成和谐的社会局面。
张驰(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名人传记,肯定不能虚构,从法律角度讲,如果有虚构,容易造成侵害名誉权。还有就是隐私权,这次《侵权责任法》当中,直接提到了隐私权,我们相对来说是比较晚的,美国在1890年已经提出隐私权了。我们关注的是对传主名誉和隐私的保护,死人活人我们都要保护。人死了就不能作为权利主体了,但对这个人的评价,对我们树立一种良好的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是有益的,所以人死后你也不能七嘴八舌,也不能去篡改事实对他乱评价。当然有的情况下是可以把他看作侵犯了另外一个主体的权利,因为对死人评价的时候,可以使活着的人心灵产生痛苦――死者本身有自己的人格尊严,活着的人也有人格尊严,你看上去是在骂死者,但可能影响到生者的利益,顺带着对生者的评价降低了,生者也可以“权益被侵害”提出诉讼。
朱妙春(著名律师):
我是借名人脱颖而出,成为鲁迅家族的首席律师,又出了一本《我为鲁迅打官司》,20年来打了七八场名人官司。对于名人传记,总的原则,就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个好像是套话,但最早的中国民法通则,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司法原则,现在还是这个原则。你写传记如果没有以事实为根据,如果对某人产生负面影响的话,那传主或家属肯定要提出来,你写的不是真实的,是莫须有的事实。最终到法庭上,法官就审查你的证据,你必须要举证,如果举证举不了就是信口雌黄就是瞎说,肯定要承担民事责任。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第二个原则问题,就是事实也不是全能写的,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这里面也有一个界定的问题,不是说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你不能把艺术家贬得一文不值,那也不行。肯定通过这本传记,人家看了以后觉得这个艺术家还是很了不起的,至于他个人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旧社会走过来的人,你说没有缺点吗?谁都有缺点,但是这个缺点写到什么份上要把握一个度,这跟动机有关系,善良的动机下,会把艺术家的形象写多一点。对于负面的东西,肯定有一个取舍问题,所以哪怕是真实的也不能全写。
《粉墨人生》那本书我看了,看后有个感觉,不是一个味,我感觉写得有点过分。写的人可能心里很痛快,但是他涉及到一个对俞老的个人评价问题。最好的处理办法是作者尽量把产生的影响消除掉,朋友或其他人最好能够劝服他。当然是先礼后兵,劝说得了劝说,劝说不了还是要诉诸法律,要讨一个说法,最终还是要消除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