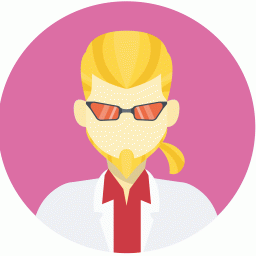闻一多:时代的鼓手
时间:2022-10-11 07:07:39

“闻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轰动中外,大抵是平静安定的,他过的是诗人与学者的生活,但是抗日战争的爆发对于他是一个转折点,他到了昆明之后似乎是变了一个人,于诗人学者之外又成了当时一般时髦人士所谓的‘斗士’。”梁实秋如是总结他的挚友。
其实,诗人的激烈与热情,学者的深刻与单纯,斗士的刚直与坚定,无论在闻一多的哪个人生阶段都不曾或离。
19世纪末的神州大地,正在战乱和羞辱中飘摇。清政府丧权辱国,外国势力虎视眈眈,政治与社会都是一片混乱。
1899年11月24日,闻一多降生于湖北浠水一个乡绅家庭。他6岁入私塾,既读“子曰诗云”,也学博物、算术、美术。
闻一多从小好读史、喜美术,十来岁就能文善画,聪敏老成。1912年,14岁的闻一多考取清华学校,一篇仿梁启超笔法的《多闻阙疑》作文,得到了考官们的惊叹。
少年意气
九年底清华生活
回头一看――
是秋夜里一片沙漠,
却露着一颗萤火,
越望越光明,
四周是迷茫莫测的凄凉黑暗。
――《红烛・回顾》
闻一多因英文成绩不佳,留了一级,但他在文字上的才华和正气凛然的性格却早早显露。
入校当年,闻一多便创办刊物《课余一览》,并担任主编。他在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已有慷慨之言:“其能存纪念于世界,使体魄逝而精神永存者,惟名而已”,“古来豪杰之士,恒牺牲其身现存之幸福,数濒于危而不悔者,职此故耳。”
清华学校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建成,学生在14岁前入校,学习八年后,全部资送美国留学,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学校突出西方教育思想,学生却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为国效力的自觉。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界发动。三千人集会游行,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北洋警察逮捕31人。清华学校位于郊区,当日没有直接卷入运动,晚上消息传来,闻一多愤慨非常,手抄岳飞《满江红》,夜里贴在学校食堂门上。
5月7日,清华学生代表团领导学校爱国运动,闻一多担任中文书记,负责起草各种文件。他在家书中说:“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
1921年6月3日,马叙伦、领导的索薪团展开罢教斗争,22所学校600余名学生在新华门前请愿。北洋军警殴打请愿者,20余人受伤。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宣布罢课,声援索薪,抗议政府。
为了阻止学生罢课,清华学校宣布6月18日举行大考,凡不参加大考者,一律默认自请退学。此时的闻一多所在的辛酉级学生即将毕业留洋,若拒绝大考,意味八年寒窗付之东流。即便如此,闻一多等29人不肯妥协,拒绝考试,黯然回乡。
闻一多等人被处分的事情,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各方压力下,管辖清华学校的外交部不得不发出部令,将闻一多等人作留级处分。
步入诗坛
不幸的失群的孤客!
谁教你抛弃了旧侣,
拆散了阵子,
流落到这水国底绝塞,
拼着寸磔的愁肠,
泣诉那无边的酸楚?
――《红烛・孤雁》
留级这一年,闻一多与梁实秋成为了终身挚友。他们与其他几位文学爱好者共同成立“清华文学社”,时常在一起交流报告研究心得。自此时起,闻一多的兴趣转向写诗与诗的理论。
1921年12月,闻一多在报告《诗底音节的研究》中首次对新诗创作与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这是他研究中国诗歌的开端。
1922年寒假,闻一多不得不接受包办婚姻,与高孝贞成婚。二人感情很好,闻一多曾写诗相赠:“爱人啊!将我作经线,你作纬线,命运织就了我们的婚姻之锦;便是一帧回文锦哦!”
1922年7月16日,闻一多去国离家,开始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留学的日子。攻读美术的同时,他开始与美国诗人结交。当时的芝加哥是美国新诗运动的中心,许多诗人聚集于此。闻一多于此时结识了罗厄尔、海德夫人、桑德堡、门罗等著名诗人。
置身于新诗运动的浓厚氛围中,闻一多对诗呈现出无比激情的状态。
读到弗来琪诗作《在蛮夷的中国诗人》后,闻一多欣喜若狂,写信给挚友梁实秋说:“快乐烧焦了我的心脏,我的血烧沸了,要涨破了我周身的血管!我跳着,我叫着。跳不完,叫不尽的快乐我还要写给你。啊!快乐!快乐!”
在为别人的诗作狂喜的同时,闻一多自己的新诗创作也有如井喷,在短短四个月时间里至少作诗63首。而在他的诗论中,不仅有专业分析,还能感受到如火的爱国激情。
1923年6月、10月,闻一多在《创造》杂志上连续发表诗论《的时代精神》《的地方色彩》,文章中他写道:“要时时刻刻想着我是个中国人,我要做新诗,但是中国的新诗,我并不要做个西洋人说中国话,也不要人们误会我的作品是翻译的西文诗……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洋固有的诗。”
在梁实秋的帮助和郭沫若的推荐下,1923年9月,闻一多的第一部诗集《红烛》问世,收录诗作103首,奠定了闻一多在中国新诗发展史的地位。
人在异乡,一颗爱国的心分外炽热,尽在诗中显现。
《红烛》向世界宣告:
红烛啊!
既制了,便烧着!
烧罢!烧罢!
烧破世人的梦,
烧沸世人的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然而沉迷于诗并不能完全对抗孤独,在闻一多与友人的通信中,时常一半堂皇的诗作,一半倾诉浓郁的孤独。所以当梁实秋赴美留学到达科罗拉多大学时,闻一多一声未吭,就提着小皮箱转学到了该校艺术系,和能够一起谈诗论赋的友人一起生活。
1924年夏,梁实秋到哈佛大学去攻读硕士学位,闻一多也决定去纽约艺术学院。
在纽约这一年,闻一多的兴趣又转移到了戏剧方面,与张嘉铸、熊佛西、余上沅等几位朋友开始共同排演戏剧。闻一多负责舞台设计与服装制作。
他们把中国戏剧介绍到美国,排演了英文古装剧《牛郎织女》《杨贵妃》《琵琶行》,其中《杨贵妃》在纽约公演大获成功,令几个年轻人备受鼓舞,彼此告语要回国发起“国剧运动”并迅速行动起来。
闻一多认为,“国剧运动”意义非小。他在给梁实秋的书信中说:“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百千倍之。杜渐防微之责,舍我辈谁堪任之!”
回归国土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死水・发现》
1925年6月1日,闻一多提前结束留学生涯,再次踏上祖国的土地。谁曾想,迎接他的是五卅惨案后的血迹斑斑。
他愤怒,提前发表了《醒呀!》《七子之歌》等诗篇,控诉帝国主义的暴行;他又为同胞的爱国热情所感动,写出《祈祷》《一句话》等爱国诗篇。
9月初,闻一多接受了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现中央美术学院)的聘请,担任教务长,同时在北京大学教授外国文学。
闻一多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建设戏剧专业。然而时局动荡,人心浮动。学府之外军阀混战,抢夺地盘,学府之内也乌烟瘴气,尔虞我诈。
1926年初,段祺瑞改组国务院,以易培基代替章士钊出任教育总长。彼时的艺专校长刘百昭因这一人事更迭辞去校长职务。在新校长委任之前,有传言说闻一多想当校长。
闻一多有心做事,却无意权位。传言令他心中不快,便立即辞去教务长职务。
在给梁实秋的信中,闻一多写道:“我近来懊丧极了,当教务长不是我的业,现在骑虎难下真叫我为难。现在为校长问题学校不免有风潮。刘百昭一派私人主张挽留他,我与太侔及萧友梅等主张欢迎蔡孑民先生,学校教职员已分为两派。如果蔡来可成事实,我认为他是可以合作的。此外无论何人来,我定要引退的。今天报载我要当校长,这更是笑话。富贵于我如浮云!我只好这样叹一声。”
剥离俗事,闻一多便退居书斋。
他的书房令所有去过的人印象深刻:四壁用黑纸裱糊,又用细金笔勾勒仿梁武祠画像的人物车马,阴森灵性而别具艺术风格。
这样一间书房成为了青年诗人的聚集地,徐志摩、朱湘、饶孟侃等人都是这里的常客。他们在这里朗诵诗文,在别具气象的环境中体会诗中妙趣。
这一年,黑屋酝酿出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二个诗刊――《晨报・诗镌》。对于此刊,闻一多壮志满怀,他认为“诗刊之刊行已为新诗辟一第二纪元。其重要当于《新青年》《新潮》并视。”
5月13日的《晨报・诗镌》发表了一篇重要的理论文章《诗的格律》,是闻一多早期建设新诗理论的总结。他主张新诗应具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文末,闻一多自信地说:“我断言新诗不久定要走进一个新的建设的时期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承认这在新诗的历史里是一个轩然大波。”
确实,他所倡导的新格律诗理论影响了为数众多的诗,并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新格律诗派,在新诗发展史上写下重要的一页。而作为他所倡理论的完美体现,《死水》更是标志着新诗的进步,开一代诗风。
潜心学术
露水在笕筒里哽咽着,
芭蕉的绿舌头舐着玻璃窗,
四围的壁都往后退,
我一人填不满偌大一间房。
我心房里烧上一盆火,
静候着一个远道的客人来,
我用蛛丝鼠矢喂火盆,
我又用花蛇的鳞甲代劈柴。
鸡声直催,盆里一堆灰,
一股阴风偷来摸着我的口,
原来客人就在我眼前,
我眼皮一闭,就跟着客人走。
――《末日》
甫回国的这两年,时局多变,闻一多也四处飘零。“国剧运动”梦想破灭,《晨报・诗镌》出刊11期后停刊,失业闲居又短暂栖身于政治大学,和梁实秋等人开办新月书店,又因不喜政治平静淡出……一腔热情几番落空,令闻一多倍感迷惘、彷徨。诗写得少了,文字中青春的热烈也消逝了。
1927年秋,闻一多应聘到第四中山大学(后南京中央大学)担任文学院外文系主任,教授西洋文学,他的同事有陈寅恪、竺可桢、汤用彤、宗白华等,皆为一时之选。闻一多接来家眷想安定下来,谁知第二年,就有桑梓劝请他去武汉大学出任文学院院长。
到武汉大学之后,闻一多由自由创作的诗人转变为谨严深入的学者。他潜心于唐诗研究,写出了《唐代文学年表》《全唐诗人补传》《全唐诗拾遗》《唐诗统笺》《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唐人小说疏证》等一系列手稿。
闻一多想要专心做学问,奈何身为院长,不得不置身于漩涡之中。武汉大学的派系复杂,权力斗争不断,闻一多性情刚直,不愿逢迎迁就,自然成了别人眼中之刺。1930年5月,受到攻击的闻一多公开贴出一张声明,说自己对于职位,如“g雏之视腐鼠”,毫不恋栈,然后坚决辞职了。
时日虽短,闻一多给武汉大学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地名――“珞珈山”,以及亲自设计的一枚校徽。
秋天,闻一多来到青岛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和国文系主任,教授中国文学和英文诗。同行的还有他的一生挚友梁实秋。
这是闻一多第四次参与创建新校了,这里有美景、有挚友、有得意弟子,闻一多度过了回国后难得的快乐时光。此处人事较为简单,他终于能继续沉潜于学术,致力于唐诗、《诗经》和《楚辞》的研究。
闻一多在给朋友吴伯箫的信中写道,“我们这青岛,凡属自然的都好,属于人事的种种趣味,缺憾太多。”短短两年内,青岛大学就发生了三次。闻一多、梁实秋作为教授,也受到了学生的攻击。有一次,闻一多和梁实秋路过一间教室,看到黑板上画了一只乌龟和一只兔子,旁边写着:“闻一多和梁实秋。”闻一多很严肃地问梁实秋:“哪一个是我?”梁实秋风趣地回答:“任你选择。”
1932年,南京政府和山东地方势力争夺青岛大学,这里成了名利场,闻一多又一次沮丧离开。
同年夏天,闻一多回到了阔别十年的清华园。十年漂泊,历经海外、北京、南京、武汉、青岛,终于还是回到了出发的地方。
这一年,闻一多34岁,在中国文学系担任教授。
此时的闻一多颇有名士气息,他的一位学生回忆说:“七点钟,电灯已经亮了,闻先生高梳着他那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的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抄稿本,像一位道士样地昂然走进教室里来。当学生们乱七八糟起立致敬又复坐下以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即刻讲。却蔼然地一笑,问道:‘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并没有谁坦直地接受这gentleman风味的礼让。于是,闻先生自己擦火柴吸了一支,烟雾在电灯下更浇重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面容。于是,像念‘坐场诗’一样,他搭着极其迂缓的腔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
闻一多十分珍惜这里熟悉而安逸的生活,全身心投入教学研究。这一时期,闻一多的研究工作,从艺术欣赏转向考据,研究的项目也愈发古远。从唐诗开始,渐次到《诗经》《楚辞》,又进入到神话、甲骨文、金文。
好景不长,流离的日子随着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炮火再次来到。闻一多无奈回乡,清华迁往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长沙临时大学。
接到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邀请他来长沙临时大学代课的书信后,闻一多立即南下,又于1938年2月随长沙临时大学步行团徒步2600余里迁移至昆明,更名西南联合大学。
六十八天的跋涉,苦则苦矣,风景奇险。闻一多别有收获,除了沿途画的几十幅写生之外,还有一部胡须。
抵达昆明后,他在群众中发出誓言:“这一把胡子,是因抗战失利,向后方撤退蓄起来的,一定要抗战胜利才把它刮掉!”
离乱将闻一多从优渥的生活中拉了出来,但他又一头扎进小楼专心于学术,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除了讲课吃饭轻易不下楼,以至于同事们戏称那座楼为“何妨一下楼”,称闻一多为“何妨一下主人”。
这是闻一多能够沉潜学术的最后一段时间了,在此期间完成了《神话与诗》《周易义证类篡》《楚辞校补》《尔雅新义》《庄子内篇校释》《唐诗杂论》等学术著作,又为编写《中国文学史稿》及中国上古文学史定了一些论文和札记。
郭沫若曾感慨:“闻一多先生的才干未尽,实在是一件千古的恨事。”“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
闻一多的学术研究,从神话到先秦诸子,从《诗经》到《楚辞》,从汉乐府到唐诗,横跨领域之广,贯穿历史之长,在现代学术史上实属罕见。他一生整理和写作数百万字,在《诗经》《楚辞》《庄子》、唐诗及神话领域的研究中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时代鼓手
请将你的脂膏,
不息地流向人间,
培出慰藉底花儿,
结成快乐的果子!
――《红烛・序诗》
由于战争的影响,物资匮乏,物价暴涨。闻一多的薪水只够全家大小八口半月开支,日子过得十分困苦,卖衣服卖书,兼课、写文章、做报告,东拼西凑,依然有一顿没一顿。不得已,这位全国知名的学者、诗人,开始治印补贴家用。
梁实秋感慨:“文人不得已而鬻印,亦可慨已!然而一多的脊背弯了,手指破了,内心闷积上股怨气,再加上各种各样的环境的因素,以至于成了‘千古文章未尽才’。”
生活苦难,再加上长期的积郁,让不问世事的闻一多走下小楼,讲起了时事。他说:“当这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我们得一鼓作气来度过危机,完成大业。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让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时代的鼓手’出现。”
1943年,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公然鼓吹法西斯主义。闻一多读后拍案而起,“《中国之命运》公开地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自此之后,几乎昆明所有的民主运动都有闻一多慨然的身影。
同时,在失望、愤怒之际,闻一多开始了解并随后有组织地学习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思想。
1944年的纪念会上,闻一多道出了他的立场:“现在大家又提出‘五四’要科学,要民主的口号,我愿意和你们联合起来,把它一起拆穿,和大家里应外合地来彻底打倒孔家店,摧毁那些毒害我们民族的思想。”
同年,闻一多经吴晗介绍加入民盟,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及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
1945年12月1日,军警特务袭击西南联大,当场杀死青年教师一人,学生三人,前后60人受伤,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全国为之震惊。
1946年2月,闻一多撰文《一二・一运动始末记》说 “‘一二・一’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但也就在这一天,死难四烈土的血给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条生路。”“愿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的历史写下了最初的一页,愿它已经给民主的中国奠定了永久的基石!”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奉命结束,师生开始北返,而闻一多仍然在昆明为民主运动奔走。
7月11日早晨,西南联大最后一批学生整装北上,当天晚上,一声枪响惊动中国――李公朴被特务暗杀了。
第二天一大早,闻一多赶到医院,抚着战友的尸体失声痛哭。他一字一顿地说:“此仇必报,公朴没有死!公朴永远没有死!”
7月13日,昆明大街谣言纷飞,人心惶惶。都说特务的暗杀名单上,下一个就是闻一多。一个朋友也专门来访,证实确实有暗杀、逮捕民主人士的计划。学联的《学生报》号外上,了一首诗:《提防第二枪》。大家都劝闻一多要小心,而闻一多早已将安危置之度外了。
昆明的空气日益紧张,对闻一多开始毫不掩饰地恐吓、威胁,而闻一多在奔忙和压力下日渐消瘦。家人劝他,他说:“现在好比是一只船,在大海里遇到了狂风恶浪,越在这时候,越要把住舵,才能转危为安。”
7月15日,闻一多要出席李公朴死难经过的报告大会。当天早晨,消息灵通的朋友再次找到闻一多,说暗杀名单的事绝对可靠,劝他千万小心。闻一多只是回答:“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慰死者。”
十点钟,李公朴先生治丧委员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开会,闻一多是出席的惟一一位教授,会场里坐满了悲愤的人,四处混杂着叼烟卷的特务。
看到肆无忌惮说笑打闹破坏会场气氛的特务,闻一多愤怒至极,不顾一切上台,即席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最后一次演讲。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进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下午的记者招待会结束后,闻一多与儿子闻立鹤在回家路上遭遇枪击。射击持续一两分钟,在闻一多身上留下十多个弹洞,闻一多当场牺牲,闻立鹤重伤。
闻一多被暗杀的消息传出之后,举国震怒。人民大众的抗议此起彼伏,数不清的团体挺身而出,反抗统治。
举国沸腾之时,闻一多的一部分骨灰被撒入滇池,永远地与滇池为伴,与西山为侣。闻一多牺牲时所着衣衫,应群众要求留在昆明。而后西南联大民主广场东的四烈士墓之前,多了一座衣冠冢,上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故教授闻一多先生衣冠冢”。
1946年9月10日,清华园工字厅后荷花池东畔小山顶上,重建钟亭,内悬大钟。为纪念闻一多,此亭被命名为“闻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