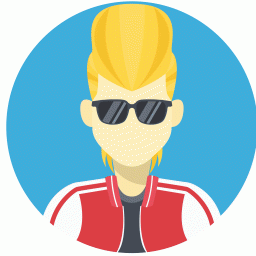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社会
时间:2022-10-10 06:52:23

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一直吸引着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在这场讨论中,值得注意的是,国外有不少学者都把中国看作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重要典型。有的人,或者出于他们敌视中国革命的立场,或者因为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缺乏了解,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散布了不少错误的观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卡尔·威特福格在他的《东方专制主义》(1957年出版)和其他一些著作中,就曾利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肆意诽谤和攻击中国革命。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对威特福格的著作还没有给予应有的批判,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另外有一些外国学者,他们的政治态度不同于威特福格,但他们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所发表的一些意见也是不正确的。例如,意大利米兰艺术学院的翁贝托·梅洛蒂教授,在他那本很有影响的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专著《马克思与第三世界》(1972年出版)中,也说什么中国是“‘亚细亚’社会的最典型例子”,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植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的集体制”。梅洛蒂的这本书尽管包含了一些令人感到兴趣和值得重视的论点,但全书的基本观点却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
本文旨在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关系,顺便对梅洛蒂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
一、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涵义与争论的症结
对于马克思所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不同理解,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种意见:(一)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原始社会或原始公社;(二)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从原始社会转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三)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继原始社会之后,既不同于奴隶社会、也不同于封建社会的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四)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的奴隶社会;(五)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混合社会形态;(六)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的封建社会;(七)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早期的一种假设,后来他已经放弃了这一概念。以上几种论者,都声称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了自己的根据。这种情况不能不促使我们认真地考虑两个问题: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前后是否有所变化?二是人们所引证的马、恩的论述,是否都能用来说明亚细亚生产方式?如果我们不是根据马、恩在不同场合所说的片言只语,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的形成过程,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作历史的考察,也许就可以在认识上找到一些共同点,从而有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中,有一点是大多数人都承认的,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原始社会史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在1847年写的《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有这样一句话:“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后来,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这句话的下面,加了一个注说:
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所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发展所由起始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土地公有的村社是从印度起到爱尔兰止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①。
这段话概括地说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原始社会史的认识过程,它对于理解马克思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历史背景以及这个概念的涵义至关重要。
19世纪40年代,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时,他们还没有形成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们指出部落所有制是人类社会的“第一种所有制形式”;同时认为,这个阶段已经出现了“隐蔽地存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社会结构只限于家庭的扩大:父权制的酋长、他们所管辖的部落成员以及奴隶。”②从50年代到了。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印度的、俄国的和日耳曼的公社,从而弄清楚了“土地公有的村社是从印度起到爱尔兰止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正是在这基础上,他们形成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
马克思在1857—1858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分析了亚细亚的、古典古代的和日耳曼的三种所有制形态,指出他们在历史顺序上虽然有先有后,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即劳动者都“把自己的生产或再生产的条件看作是自己的东西”③。也就是说,劳动的主体和劳动的客观条件(主要是土地)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统一。劳动者对土地的关系,是通过他作为部落成员这种媒介发生的。不过,由于部落的天然性质和经济条件不同,这三种所有制形态又表现出重大的区别:在亚细亚形态下,是采取公有财产形态,土地属于公社所有,个人只是占有者,根本没有私有的土地财产;在古典古代的形态下,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同时并存,只有国家公民才能成为而且一定成为私有者;在日耳曼的形态下,个人财产是基础,公有财产仅是个人财产的补充物,而公社只存在于个人土地所有者的相互关系中。马克思认为,在罗马人和日耳曼人那里,由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发展,原始的社会形态很快就被破坏了。但在亚洲一些国家,由于“奴隶制在这里既不破坏劳动的条件,也不改变本质的关系”,原始公有制因而得以长期保存下来。马克思把这种以原始的公社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叫做亚细亚生产方式.他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④
当马克思最初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的时候,他是把它当作原始的社会形态来看待的。但它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原始共产社会(即氏族社会)是两回事。这种生产方式,如果仅就其所有制而言,是一种部落的公有制,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称它是“原始共产主义”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前阶级社会,因为在亚细亚所有制下面,已经产生了统治和奴役的关系,已经有了剥削公社剩余劳动的专制君主。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明确指出在亚细亚形态之下,“单个的人从来不能成为所有者,而只不过是占有者,实质上他本身就是作为公社统一体的体现者的那个人的财产,即奴隶”⑤。恩格斯在1877年写的《〈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中也说:“在自发的公社中,平等是不存在的,或者只是非常有限地、对个别公社中掌握全权的成员来说才是存在的,而且是与奴隶制交织在一起的。”⑥
1877年,摩尔根写成《古代社会》一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读了《古代社会》之后,对于原始社会史的认识有了重大的改变。例如,马克思原来认为人类最初的社会组织是由家庭发展而成为氏族,后来才了解“氏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自然形成的原始形式。由于氏族纽带的开始解体,各种各样家庭形式后来才发展起来”⑦。又如,马克思原来对于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公社并没有严格加以区别,而是笼统地把所有的公社土地所有制都说成是公有制。但在1881年2月底至3月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他已经指出“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它们有好多种社会结构,这些结构的类型、存在时间的长短彼此都不相同,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马克思分析了农村公社公有和私有的二重性,指出它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⑧。
由于对原始社会史认识的深化,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再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是人类历史上原始的社会形态了。因为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之前,有一个以氏族公社为典型的原始共产社会阶段。在这个氏族社会阶段,是没有阶级、也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所以,《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那句话,也就不十分确切了。这就是为什么恩格斯后来觉得需要在这句话下面加一个注予以修正的缘故。
1883年1月,马克思逝世。恩格斯在1884年3月至5月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他把这看做“在某种程度上是执行”马克思的“遗言”。在这部光辉著作中,他科学地分析了人类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揭示了原始公社制度的解体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形成的过程,阐明了国家将随着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彻底胜利而消亡的历史必然性。书中写道:“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⑨至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关于资本主义以前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顺序,马克思生前没有来得及完全确定,这一工作终于由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完成了。这个顺序就是:原始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应当指出的是,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不再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是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了,但他们并没有改变早先的一个重要观点,即东方一些国家(包括俄国)长期保存着公社组织和公社土地所有制。而且,他们在自己的文字中,有时还仍然把公社土地所有制称为“原始共产主义”的所有制。例如,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二稿中,就写道:“我顺便指出,俄国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形式是古代类型的最现代的形式,而后者又经历过一系列的进化。”(三稿中删去了这段话)恩格斯在1884年2月16日给考茨基的信中,谈到爪哇的公社时,也写道:“那里的原始共产主义,像在印度和俄国一样,今天正在给剥削和专制制度提供最好的、最广阔的基础。”⑩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俄国和爪哇还处在原始共产社会阶段,而只是说那里保存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带有原始共产主义的特征。但是,从我们今天看来,这种说法并不十分科学。爪哇的情况不大清楚,至于俄国,按照马克思自己在给查苏利奇信中所说的,农村公社已经有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二重性,即便不考虑专制主义的上层建筑,单就所有制而言,也不能说是“原始共产主义”的了。
在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中,有的人由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有关亚细亚所有制的论述没有做具体分析,而把亚细亚所有制和作为特定社会经济形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完全混为一谈,结果是:或者否认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属于阶级社会的范畴,或者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是亘古不变的特殊社会。应该说,这是争论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一个重要症结。
所有制是决定生产方式性质的重要因素,但所有制的形式并不等于就是生产方式。比如说,国有制是一种所有制形式,但是它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可以有不同的性质。公社所有制既有氏族公社所有制,也有农村公社所有制,前者属于原始共产社会的生产方式,后者则是从原始共产社会向私有制社会过渡的阶段,而在一些国家中,它还可以长期保存在阶级社会里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亚细亚的所有制看成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础,但他们在分别使用这两个概念时,涵义是有区别的。在马、恩著作中,只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第l卷第一章直接提到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这两个地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都是指特定的社会经济形态。至于马、恩经常谈到的亚细亚的所有制,并不能都当作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同义语来理解。因为他们在谈到亚细亚的所有制时,在大多数场合下,着重讲的是原始公有制的财产形态。而作为特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内容,则要比这种公有制的财产形态复杂得多。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50年代形成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的时候,他们已经指出以这种生产方式为特征的共同体,公有制的财产形态是和奴隶制的剥削与压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后来,恩格斯在《美国工人运动》中,更明确地说:“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即与其说是群众被剥夺了土地,不如说他们的人身被占有。”⑾在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中,有些人往往只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亚细亚所有制称为“原始共产主义”的论述,而另一些人则强调马、恩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阶级压迫形式是奴隶制,结果就各执一词,相争不下。其实,只要把亚细亚所有制和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两个概念作适当区别,分歧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除了直接对亚细亚所有制和亚细亚生产方式所作的分析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经常谈到亚洲社会的一些特点,例如农村公社和公社土地所有制的长期存在,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专制主义的统治等等。对于这些论述,我们也不能统统归结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说明;更不能根据这些论述,得出亚洲各国自远古以来始终停留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结论。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排斥亚细亚所有制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某些特征也有可能在封建社会里继续保存下来.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印度历史上存在过封建社会的意见,但他在《资本论》第3卷分析封建的劳动地租时,曾举印度为例说:
在这里,按照假定,直接生产者还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即他实现自己的劳动和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所必需的物质的劳动条件;他独立地经营他的农业和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农村家庭工业。这种独立性,不会因为这些小农(例如在印度)组成一种或多或少带有自发性质的生产公社而消失,因为这里所说的独立性,只是对名义上的地主而言的⑿。
这里显然是把农村公社制度和封建制的地租剥削联系起来的。我们再看看列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列宁是承认俄国保存着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一些基本特征的,但他并没有认为俄国是亚细亚社会,而是始终肯定沙皇俄国是一个农奴制的封建社会。他在《社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说:“不‘清洗’中世纪的(部分是封建式的,部分是亚洲式的)土地关系和土地制度,农业中的资产阶级变革便不可能发生.”⒀更是明显地把亚细亚的土地所有制纳入“中世纪”的范畴。
二、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社会
马克思所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是什么?自从1928年马札亚尔出版《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以来,不少学者对此发表过各种各样的意见。梅洛蒂在《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中说:“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社会的概念,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没有土地私有制;即使退一万步,至少,土地也是属于国家所有。第二,亚细亚社会的基础是村社制,每一个村社通过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而达到自给自足.第三,中央集权起着支配作用。”⒁这是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
上述这些特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东方各国的历史实际’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就中国的情况来看,如果说历史上也存在过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一些特征的话,那就是西周的奴隶制社会。
西周的基本社会单位是邑、里或书社。《礼记·王制》:“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尔雅·释言》:“里,邑也。”《商君书·赏刑》:“〔武王〕裂土封诸侯,士卒坐陈者,里有书社。”无论是邑、里或书社,都是一种地域性的农村公社组织。《逸周书·大聚解》:
以国为邑,以邑为乡,以乡为闾,祸灾相恤,资丧比服。五户为伍,以首为长;十夫为什,以年为长;合闾立教,以威为长;合旅同亲,以敬为长。饮食相约,兴弹相庸,耦耕俱耘。男女有婚,坟墓相连,民乃有亲。六畜有群,室屋既完,民乃归之。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畜五味以备百草。立勤人以找孤,立正长以顺幼,立找丧以恤死,立大葬以正同,立君子以修礼乐,立小人以教用兵,立乡射以习容和,猎耕耘以习迁行。
这段文字,可能搀入了一些春秋战国时代的材料,但它却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农村公社的田园生活的生动图景。这种农村公社一般都由若干个体家庭组成,“在国中则始于一里二十五家,在野则始于四井三十二家”⒂。公社的土地所有制就是所谓井田制。《周礼·地官·小司徒》:“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滕文公使毕战向孟子打听关于井田制的情况,孟子还讲得出一个大概:“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⒃私田即村社农民的份地,公田则是村社的共有地。份地是要定期重新分配的。《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是故圣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妇受田百亩……司空谨别田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得独乐,烧确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主易居,财均力平。”这种情况,正符合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所有制形态的特征:“不存在个人所有,只有个人占有;公社是真正的实际所有者;所以,财产只是作为公共的土地财产而存在。”⒄
马克思说,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所有制形态,“本身可能以十分不同的方式实现出来”。“例如,跟这种形式完全不矛盾的是,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惟一的所有者,实际的公社却只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⒅。西周的井田制也具有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和奴隶主土地国有制的双重形态。《诗经·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奴隶主土地国有制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由于亚细亚财产形态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公社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属于最终作为个人而存在的更高的共同体,而这种剩余劳动既表现在贡赋等等的形式上,也表现在为了颂扬统一体——部分地是为了颂扬现实的专制君主,部分地为了颂扬想像的部落体即神——而共同完成的工程上”⒆。西周农民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就是通过藉田的形式,被“最终作为个人而存在的更高的共同体”所攫取的。《国语·周语》记“宣王即位,不藉千亩”,虢文公竭力劝阻,其理由是藉田关系到“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事之供给于是乎在”。“上帝之粢盛”,可以说是为了颂扬“想像的部落体即神”;“事之供给”,则是满足以周天子为首的奴隶主阶级的需要。
如果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映了西周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周天子是全部土地的最高所有者,那么“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则是表示周天子对于全国臣民的一种人身占有关系。村社成员不但不拥有土地财产,而且他们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就是专制君主的财产和奴隶。这种和奴隶制没有多大区别的阶级压迫形式,在人殉制度上也明显地表现出来。西周和商代一样,存在着残酷的人殉制度。殉人大多是奴隶,但也有的并不是奴隶。直到春秋时代,在奴隶主贵族中间,还有以妻妾家宰殉葬的。秦穆公甚至不顾国人反对,用秦国的“三良”为殉。这种情况说明,在古代中国,一家之内,妻妾子女不啻是父家长的奴隶;一国之内,臣民也不啻是国君的奴隶。
我们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一些论述适用于西周时代,是就其主要特征而言的。至于西周社会的实际情况,当然要比马、恩的论述复杂得多。可以举出它们之间这样的一些不同之处:
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⒇。这一点,曾被威特福格加以歪曲,得出所谓东方“水利社会”的结论。中国古代的水利灌溉与农业的发展虽然关系也很密切,但在具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特征的西周时代,水利灌溉事业并不发达;倒是在农村公社已经瓦解的战国和秦汉时代,水利灌溉事业才发达起来。
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古典古代的劳动奴隶制得到充分发展,古代东方则是家庭奴隶得到充分发展。西周时代除了家庭奴隶制比较发展之外(家庭奴隶并不是完全不从事生产,而是作为家庭的组成部分,间接地构成生产的基础),还存在着相当数量
第三,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由于误把家庭当作人类最初的社会组织,曾认为亚细亚所有制的“第一个前提首先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家庭和扩大成部落的家庭,或通过家庭之间互相通婚[而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联合”[21]。后来,他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农业公社’是最早的没有血统关系的自由的社会联合”[22]。马克思的后一个看法无疑是正确的。西周的农村公社实质上也是一种地域组织,但由于西周存在着宗法制度,不少农村公社还保留着比较牢固的血缘纽带。所谓“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23],说明当时的阶级关系还裹着一层宗法制的血缘外观。
第四,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上层建筑是东方专制制度,它不同于古典古代的贵族共和政体.西周奴隶主国家的统治虽然具有专制主义的色彩而非共和政体,但在贵族和自由民内部,还保存着原始民主的残余。春秋的国人可以议政,就是例子。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一方面把国君看成是“神之主也,民之望也”,“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如果遇到“困民之主,?T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民“出其君”也是合理的[24]。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一些论述,与古代中国的历史实际不尽符合,这是不奇怪的。如果它们完全合辙,那倒不合情理了。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时候,我们既不能削足适履,按照马、恩的论述来套中国的历史;也不能因为二者不尽符合,就忽视马、恩的论述的指导意义。
在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在被西方殖民者打开大门之前,始终是一个“亚细亚社会”,并且有它特殊的阶级结构。例如,梅洛蒂的《马克思与第三世界》说,中国“直到上一世纪为止,亚细亚社会的典型结构还多少原封未动地保持着,其基础是孤立的、从事自给自足生产的村社,在其顶峰是一种专制权力,它一面剥削村社,同时又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程度的效率发挥水利管理的重要职能。从理论上说,所有土地,或者说无论如何大部分土地,属于国家,而实际上国家的官僚们是受益者而且构成了真正的剥削阶级”[25]。对于梅洛蒂这样一个外国学者,我们不能要求他对中国历史有翔实的了解,但是他在上面所表述的基本观点,却不能不说是对中国历史的一种严重歪曲。
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性质,是封建社会而不是什么“亚细亚社会”,这是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早已解决了的老问题。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也证实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础是农村公社和公社土地所有制。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以井田制为标志的农村公社和公社土地所有制就已经瓦解。在这种情况下,要说中国直到上一世纪“还多少原封未动地保持着”亚细亚生产方式,这无论如何是讲不通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大致有三种:(一)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二)自耕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三)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在这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当中,地主土地所有制是支配的形态,它和自耕农的小土地所有制都属于私有制的范畴,而与亚细亚生产方式毫不相干。封建土地国有制在某种意义上虽然可以看作是亚细亚所有制的孑遗,但由于农村公社和公社土地所有制早已瓦解,它也很难说还具有公有制的性质。这从秦汉时代掌管国有土地的少府职务上也可以得到证明。《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应劭《汉官仪》:“少者小也,小故称少府。王者以租税为公用,山泽陂池之税以供王之私用。”还应指出的是,在历代封建社会中,除了“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26]这种情况之外,一般说来,土地国有制在全国的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关系发展的规律是: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地主阶级手里,贵族、官僚、地主不仅竞相兼并农民的土地,而且经常侵吞国有土地。
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常被一些西方学者用来作为证明中国是一个“亚细亚社会”的论据。梅洛蒂也是这样看的。但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作为一种政体,和亚细亚生产方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既可以建立在奴隶制的生产方式之上,也可以建立在封建制的生产方式之上。恩格斯说:“东方的专制制度是基于公有制。”[27]又说:“古代的公社,在它继续存在的地方,在数千年中曾经是从印度到俄国的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28]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根本不是公有制和农村公社。恰恰相反,从秦朝开始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是在农村公社已经瓦解、私有制完全取代了公有制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史表明,建立在地主制的封建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专制主义的国家机器,要比基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上的专制主义的国家机器强有力得多。
梅洛蒂否认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奴隶主和奴隶、封建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对立。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亚细亚社会”中,真正的剥削阶级是“官僚集体”。由于这个“官僚集体”是某些社会职能(例如水利灌溉工程的管理等等)的担当者,因而它就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和历史的延续性。从这样的历史分析出发,梅洛蒂声称今天中国仍然是建立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官僚集体制”的国家。梅洛蒂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歪曲是不值一驳的。这里要指出的是,他对于中国历史上阶级关系的分析,也是非常错误的。无论是中国的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都不存在一个特殊的“官僚阶级”。在商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贵族世官世禄,他们既是剥削阶级,又是统治阶级。普通的平民和奴隶要上升到统治阶级的行列中去,是非常困难的。战国时代,新兴地主阶级代替奴隶主贵族掌握了政权,废除了世官世禄制度,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官僚系统。从秦汉到明清,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不断强化,官僚的队伍也日益膨胀。比起奴隶主国家来,地主阶级国家的统治基础无疑要宽广得多。但历代封建王朝的各级官吏,不论其出身如何,按其社会本质而言,都不过是地主阶级的工具。个别官吏为了维护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虽然有时也对那些不法的地方豪强实行一定的限制和打击,但这并不改变他们作为地主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从对农民的剥削来看,各级官吏合法和非法的所得,也都是地主阶级所攫取的农民剩余劳动的一部分。梅洛蒂在他的书中说:“在东方专制制度下,特权阶级并不占有土地或人,而是掌握一种公共职能,即作为国家——惟一的土地所有者——的代表而索取地租。”他还引用马克思如下的一段话作为自己的论据:
[正在亚洲,]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那未,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说,不会再有什么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在这种情况下,依附关系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除了所有臣民对这个国家都有的臣属关系以外,不需要更严酷的形式[29]。
但历史事实恰恰反驳了梅洛蒂的观点。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除了在授田制和均田制下面,存在过地租和赋税合为一体的情况以外,一般说来,自耕农民要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而佃农则要向地主缴纳地租,田赋和私租历来是分开的。地主阶级不但占有大量土地,还占有大量劳动人手。农民除了对封建国家的臣属关系以外,往往还以更严酷的形式依附于地主阶级。没有当官的地主虽然也要缴纳赋税,但他们经常把这部分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封建国家即使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农民也得不到多少实惠。历代政论家所发出的“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30]、“官取其一,私取其十”[31]等等的慨叹,都说明在正常的情况下,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对于农民剩余劳动的再分配,前者所占的比例要比后者大得多。梅洛蒂抹煞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认为只有封建国家的官吏才是“真正的剥削阶级”和“受益者”。只要稍微对中国历史有点常识的人,都不难了解这种说法有多么荒唐!
梅洛蒂书中还有另一些荒谬的观点,例如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没有能力独立自主地发展的生产方式”;中国这样的“亚细亚社会”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就还有可能再继续存在许多世纪”;如此等等。在这篇文章中,限于篇幅,我们对此不准备——加以评论。但是有必要指出:这些似曾相识的说法,竟然出之于一位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并且对第三世界的历史命运表示关心的作者口中,实在令人感到遗憾。这里,不妨引用一下马尔科姆·考德威尔在《马克思与第三世界》英译本编者前言中对梅洛蒂的批评。考德威尔写道,在自命为马克思信徒的那些西方人中间,“欧洲中心主义”表现出相当大的力量,梅洛蒂“也不能免于这一可想而知的影响,正如他对中国革命的评论中所表现的”。梅洛蒂“颂扬西方技术是未来‘真正的’革命的最终保证”,表明他未能摆脱“这种世世代代根深蒂固的幻想:认为世界是以白种人的富国——它们的行动、倡议、决定和方向——为中心而运转的”。考德威尔接着说:“当西方世世代代盛行这种不费力气的、深信不疑的优越感的时候,亚洲的革命者也许现在大可对这种不可救药的思想废渣取笑一番。”这些中肯的批评,倒是值得梅洛蒂教授认真考虑的。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表明中外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的理解,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梅洛蒂在他的书中,把这种分歧归结为“单线论”与“多线论”的对立。
应当承认,在国内外以往的历史研究中,是存在把五种生产方式简单化和僵化的倾向的。这种教条主义倾向,严重地妨碍了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自从恩格斯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来,已经过去将近一百年了。这近百年中,世界范围内考古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的许多新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为我们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宝贵材料。对于这些新的材料怎样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是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但是,用“多线论”与“单线论”的对立来概括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认识,我认为并不恰当。因为无论是“多线论”或“单线论”,都可以作不同的理解。“多线论”可以理解为否认不同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的共同性。而这种共同性,正是我们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列宁曾经指出:“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它把‘生产关系’划为社会结构,使我们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一般科学的重复律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32]“多线论”的提法,反映不出社会制度的这种重复律。当然,不同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的共同性,又是具有无限丰富生动的内容的。正如列宁所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33]“单线论”的提法,则很容易被误解成单一的模式,从而忽视了不同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的多样性。
在梅洛蒂“多线论”的图式中,中国、印度、埃及等国都属于“亚细亚社会”,俄国则属于“半亚细亚社会”,它们都没有经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世界史上经过奴隶社会阶段的,只有古代希腊罗马。这种意见,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新的观点,不过它反映了对五种生产方式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并不能真正解决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问题,当人们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重新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时,有的人难免又要回到某种老的观点上去。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古代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欧洲看作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典型,但是他们并不认为,奴隶社会只存在于古代希腊罗马,封建社会只存在于中世纪欧洲。如果是那样,他们也就不会主张“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了[34]。马克思说:
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35]。
这里的“古代社会”,也就是奴隶社会。马克思曾经明确说:“在古代和中世纪,奴隶制或农奴制形成社会生产的广阔基础。”[36]恩格斯也多次指出,奴隶制是古代社会阶级压迫和剥削的主要形式。既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一样,都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怎么能说所揭示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只存在于古代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欧洲呢?
我们说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不外乎有两层意思。第一,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37]。第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决不是孤立的、个别的现象,而是在世界范围内有重复性和常规性的现象。恩格斯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就曾指出:“在古代,正像现代在许多落后国家、甚至美国南部一样,劳动者是主人的奴隶。在中世纪,劳动者是土地占有贵族的农奴,直到今天这种农奴在匈牙利、波兰和俄国都还残存着。”[38]当然,奴隶制和封建制的这种重复性和常规性,并非指完全同一的模式,也不能理解为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必须经过这两个社会发展阶段,概莫能外。因为,“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39]。至于有的国家和民族因为历史条件的不伺,越过了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阶段,当然也是不足为奇的。
对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历史,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一种方法是以古代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欧洲为惟一的模式,或者把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削足适履”式地纳入这种模式;或者因为看到其他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有和这种模式不一致的地方,就宣布这些国家或民族没有经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另一种方法是在承认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可以有不同类型的前提下,既看到了不同国家或民族经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共同性,又看到了它们之间奴隶制和封建制类型不同的多样性。我们赞成后一种研究方法。人类历史的发展不能说是多线的,但不论哪一种社会制度,却都是多模式的。
长期以来,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采取简单化和公式化的理解,形成了一种不正确的认识:奴隶社会一定要奴隶占人口的大多数;封建社会一定要从领主制开始。按照这样的公式来要求,历史上可能就没有一个奴隶社会,而封建社会则只存在于少数的民族和国家。这样,要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共同的规律,也就很难了。中国的奴隶社会不同于古代希腊罗马,中国的封建社会也不同于中世纪欧洲。如果一定要用欧洲的模式来要求中国,那么中国就不但没有奴隶社会,也没有封建社会。但中国自秦汉以后(或者像魏晋封建论者所说从魏晋以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租佃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成为支配的形态,难道这不能说是封建社会的一种类型,反而可以把它和亚细亚生产方式混为一谈吗?有些论者承认日本有封建社会而不承认中国有封建社会,我们且不说日本的封建社会究竟和中世纪欧洲是否同一种类型,就从日本封建社会的各种制度深受中国的影响来看,这种说法也是很难成立的。
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40]又说:“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41]可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结合的方式和方法,是我们据以判断社会经济形态性质的最主要的标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只要是具备奴隶制或封建制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并且这种生产方式已经成为支配的形态,我们就没有理由因为它们不同于古代希腊罗马或中世纪欧洲而拒绝承认它们是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原始社会瓦解之后,是否既可以发展为奴隶社会,也可以发展为封建社会?奴隶制和农奴制是相去不远的两种剥削形式。马克思说:“假如把人本身也作为土地的有机附属物而同土地一起加以夺取,那么,这也就是把他作为生产的条件之一而一并加以夺取,这样便产生奴隶制和农奴制,而奴隶制和农奴制很快就败坏和改变一切共同体的原始形式,并使自己成为它们的基础。”[42]由此看来,马克思是认为从部落所有制的原始社会既可以产生奴隶制,也可以产生农奴制的。恩格斯也说:“毫无疑问,农奴制和依附关系并不是某种特有的中世纪封建形式,在征服者迫使当地居民为其耕种土地的地方,我们到处,或者说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例如在特萨利亚很早就有了。”[43]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农奴制,是指部落之间由于征服而产生的原始农奴制。它是中世纪农奴制的前身,并非就是“中世纪封建形式”的农奴制。恩格斯说,这种原始农奴制曾经使他和另一些人“在中世纪农奴制问题上感到迷惑不解;人们很爱轻易地单纯用征服来说明它,这样解决问题又顺当又省事”。恩格斯这些话的意思,正是要说明这种原始农奴制和中世纪农奴制其实是有区别的。在另一个地方,恩格斯曾经把9至1l世纪德国的农奴制,说成是“古代日耳曼奴隶制的继续”[44]。他所说的“古代日耳曼奴隶制”,也就是日耳曼人的原始农奴制。第二,有了奴隶制,并不等于就是奴隶社会;有了农奴制,也不等于就是封建社会。在原始公社解体的地方,虽然有可能产生奴隶制,也有可能产生农奴制,但是形成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需要比形成奴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高。因此,无论是从逻辑的顺序说,或是从世界上多数文明国家的历史看,奴隶社会都是先行于封建社会。迄今为止,我们还找不出有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是从封建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的。
人类历史的发展有着共同规律,而这种共同规律是通过各个民族和国家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表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45],使我们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出它的规律性来。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认真研究历史发展的多样性,阐明它的规律性,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9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9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668、669页。
⑦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版所加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90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32、448、450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72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2页。
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8、259页。
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90、891页。
⒀《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55页。
⒁ 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高?、徐壮飞、涂光楠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
⒂ 金鹗:《求古录礼说·邑考》。
⒃《孟子·滕文公上》。
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1页。
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3页。
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3页。
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4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2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49页。
[23]《左传》桓公三年。
[24]《左传》襄公十四年。
[25] 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高?、徐壮飞、涂光楠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
[26]《三国志·魏志·司马朗传》。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681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0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91页。
[30] 荀悦:《汉纪》卷8。
[31]《陆宣公集》卷22。
[32]《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20页。
[3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90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8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87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40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3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2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92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04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90—491页。
[43] 恩格斯1882年12月22日致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31页。
[44] 恩格斯1882年12月16日致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25页。
[45]《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