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本的壮游计划:即使受伤了,也要继续我的旅程
时间:2022-09-18 08:5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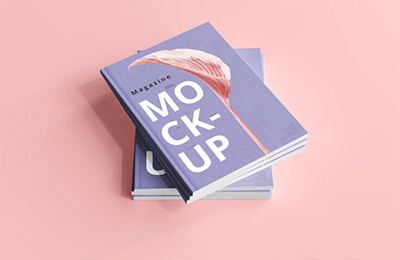
在实体书店买过书的人,大概都有这样的经验:同一版本的书,左右手各一册,对比它们的印刷质量、有没有污渍、边角会不会破损;这个过程有时甚至来回几次,端视书架上的数量多寡,直到比较出“目前可以得到的品相最好的一本”。虽然那些瑕疵并非我们造成,但最后的挑选动作,决定了一本可以跟我们回家,而其它继续留在书架上;几轮“汰选”后,总有那么一些一直无法受到青睐,它们也变得更加伤痕累累,最终只能回到出版社的仓库,从此不见天日。
如果说,一本书从诞生直至被阅读,才真正完成了一次生命,那这些回头书,都是夭折的孩子。“如果我们都觉得书很重要,而书的任务是被阅读,就不应该让它因为受伤了而旅程就此打住。”因为这样的想法,陈夏民决定让受伤的逗点文创结社的孩子,再出去好好玩一次。这是他在2012年底开始执行的“书本的壮游计划”。
以邮局纸箱为行李箱,出发!
处理回头书的方法有很多种,譬如销毁、捐赠、卖掉、在摆摊时当二手书出售……这些在陈夏民看来都太被动了。“因为捐出去之后我不确定它们是不是只是换一个地方摆着而已,如果它们只是从仓库到另一个仓库,那我还是会觉得有点难过。我希望主动一点,让书可以被看见。”于是他开始统计仓库里回头书的数量,为它们准备一个邮局的纸箱充当行李箱,为它们安排地点旅行。
他在Facebook上贴出活动内容,很多读者开始转贴分享,头一两天他就收到了几十封信,到目前为止,共有七十多个团体或个人表示要参加。他们,就是书本的导游。报名时,导游需要注明申请的数量(也就是读者人数)和希望阅读的书。“我们在轮的时候,没有办法顾及到每一位申请者,所以他不一定会拿到他想看的,但他还是愿意加入这个活动。因为回头书的数目有些是十本,有些是二十本,有些是数十本,我就必须按他申请的数量来分配,后面可以再让他拿到别的书。”
“书本的壮游计划”简单来说,就是导游拿到书之后,发给大家,他的朋友们一起看,看完了、回收好以后,装箱,再直接寄给下一个人。听起来简单,但最繁琐的就是如何分配路线,以及联络导游。“我们原本希望导游能协调下一位导游,这样活动就能自己运行下去。但大部分人要另外找到一个人愿意负担那十本甚至四十本书的分配,其实有点困难。所以就变成中间的协调跟沟通都由我们来做。另外,书发出去之后,可能回收的效果没有那么好,我们就得一直去提醒,一直去催:你可以准备送到下一个地方去了。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成本在这上面。一开始是我一个人做,但后来真的完全没办法,所以就请了我的好朋友来帮忙,请他定期联络。我们现在手上有七十几封信,也不过才处理到十几封而已。所以这个工程很浩大,得要长期抗战。”
书本在一个地方逗留约一个月后,导游回收、装箱,再寄往下一个地方。台湾有一种固定价位的包裹,用邮局的箱子,第一次寄只要100块(新台币),两天内就能寄达;箱子下次重复利用还有邮费折扣。得益于这项邮局服务,这个壮游计划才能够成行。
爱书人接力,全台走透透
参与“书本的壮游计划”的人,遍布全台湾,从台北、台南、苗栗到台东、花莲,甚至连澎湖也有人报名;大多为团体报名,尤以学校为多,但也有个人和二手书店的读者,希望跟生活圈的朋友一起分享。为了便于前置作业,每个包裹一整箱都是同一本书,这也使得大家可以同时读一本书,一起讨论。
现在壮游途中的,以太宰治的《御伽草纸》、伊格言的《你是穿入我瞳孔的光》和阿图的《九份·猫体诗》这三本为主。“这个活动有点复杂,我现在也没办法立刻再开出所有出版品的项目。要等到一个阶段后,再增加新的书进来。其实书都整理好了,只是一旦多送出去一箱,后面又是一整串联络的事情。在人力有限的状况下,只能够先做目前这几本回头书。”
那什么时候会让书本回家呢?陈夏民原本计划,至少走到第十个地点,才让书本回来,但依照目前联络的复杂状况,可能会在第五或第六个地点之后就请导游先寄回来,看看有什么方式可以让路线更简化。但不管怎样,“一个包裹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呆很久,它的旅行地点会比较多,这才叫壮游。”
阅读的灵感让书变得不一样
最初公布的游戏规则里有这样一条:读者看完之后,请把这一本书带给你的启发或灵感(可能是一张照片、一张纸条、一篇短文章等),连同这一本书一起装进“封口袋”交还给导游。陈夏民说:“这类活动我就很害怕会变成老师要求学生一定要读,然后要写几百个字心得的状况。其实阅读会有很多的灵感,那个灵感不一定要从文字方面着手。我做这个活动,只是希望大家可以放轻松地去读这本书。我看到有些人的感想就很奇妙,像很多学生看了《九份·猫体诗》,他们就会去写跟猫咪有关的诗,或者是拍猫咪的照片,还有画画的。而且他们写的时候是用自己的信纸去写,然后贴贴纸,或画卡片。我觉得很可爱,也很浪漫。”
同一本书,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当这些想法全部被放在那本书里面,再寄到下一个地方去,另一个人拿到这一本书的时候,就有点像瓶中信。“你会拿到一封信,那不一定是写给你的,可是你会有一种很有趣的阅读感受。”所以,出去是一模一样的书,但只要经过一次阅读,书袋里就增加了不同的内容,沾染了读者的思绪和温度。
那,回来之后还是要被销毁吗?这样也太悲伤了吧。“但是也值得了。”陈夏民话锋一转,“应该是等到它们全部都回来以后,看有没有一个方式,展览或是什么,然后结束之后进行义卖或者销售。因为那时候每一本书就不是只有书本身了,它还有很多的信、照片和读者的想法在里面。想想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延续这个阅读的形式,或者是,看有没有人要带它们回家。”
书作为载体,在阅读过程中,轴心会歪掉,页面可能会散开、产生皱褶,为了完成使命,它同样会受伤。“因为这个载体是书,我们对它会怀抱着浪漫一点、拟人化的想法,但这就是时间的作用,至少,它是被阅读过了。”
我问了陈夏民一个不浪漫的问题,我相信,那是所有办过类似活动的出版业者都会关心的问题,而他的想法是:“我们在做很多活动的时候,一开始都会这样想:希望读者如果看了喜欢的话,会去买。但是因为这里面有些书已经绝版了,他想买也买不到。所以就实际的获利来讲,事实上也很难。但是另一个方面,如果读者可以透过这样的活动、这样的书认识逗点,对逗点这个品牌形象也蛮好的,因为越来越多人认识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