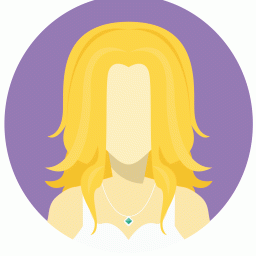《幸运是我》:能看到未尝不是幸运
时间:2022-09-04 03:44:58
很久没看过这么温情的影片了,《幸运是我》讲的是一个独居老人与青年租房客从路人到邻人再到亲人的故事,说起这等人物关系和故事框架,实在很容易煽情催泪,难得它却拍得十分温和而克制,颇具香港市井电影的底蕴精神。
《幸运是我》于去年暑期档上院线,曾被称作“全国暖心公映”,但寥寥可数的排片量,票房冷清,未及进入广大影迷视野便匆匆下线。我能偶尔看到它,还是从娱乐资讯里面捞来的消息:两届香港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惠英红,在这部电影里被业内人士认为贡献出了“女神级”的表演,在纽约举办的第39届亚美国际电影节斩获2016年亚洲传媒人道主义奖,并且已经被提名为2017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人选。
影片时长近2小时,不知不觉看下来,观影体验非常平淡自然、轻松舒服,片尾字幕出现时,竟有些意犹未尽的不舍,如果时间充裕,真想再刷两遍。这等耐看程度,女主角惠英红自是功不可没,年届六十与年轻新人演员陈家乐搭戏老少配,被网络影评人赞为“2016年度华语电影最佳组合”,这美誉也颠覆了惠英红阿姨出道以来拳打脚踢英姿飒爽的“打女”形象。跟大多数非商业片一样,《幸运是我》主题描绘了一个恒久远的人类困境――孤独的人们如何克服各款各式的孤独状。
在这个抱团取暖的故事里,蕴含着城市人文关怀、珍惜人际沟通、反映老年社会、克服认知障碍等多项叙事表达。陈家乐扮演的阿旭在母H去世后,来香港寻找与母亲离婚多年的父亲。虽然电话联络上了,可父亲并不急于见他。举目无亲的阿旭失业又被房东退租,无所事事地四处游荡,偶然在街头邂逅惠英红所饰的老妪芬姨。此时,芬姨的房客突然搬走,阿旭恰急需住处,因为如果没有居住证明他就找不到工作。于是他死皮赖脸一波三折地租住进芬姨家。脾气古怪的芬姨和年少轻狂的阿旭,难以在同一屋檐下平静相处,两人摩擦不断,阿旭甚至一度离去。然而,在这人情寡淡冰冷的城市里,两人间不断发生的种种摩擦,正是温暖人性的助燃剂。
阿旭了解到芬姨的孤单落寞,于是带上她到自己工作的社区服务中心去上班,细心的同事发现芬姨患有阿尔茨海默病,阿旭陪她就诊,监督她按时服药,这让他们逐渐相互依赖。阿旭在朋友帮助下找到父亲商铺,父亲早已另有家室,阿旭带同父异母的小弟弟出去玩,弟弟食物过敏,这个意外让他们父子情分彻底决裂,父子间对话只能通过警察传来递去。芬姨目睹这一幕,先是大声谴责其父:“连儿子都不认,你还算人吗!”继而对阿旭柔声抚慰:“没关系,你还有我这个妈,我们回家。”泪流满面的阿旭倚到她臂膀上。最终,他们成为情同母子也形同母子的一家人。
《幸运是我》没有大场面,少有戏剧冲突,更无炫目特效,处处是细水长流般的日常琐屑、小民纠葛和人情世故,有寒凉也有温暖,寓意繁复,信息量密集。在芬姨和阿旭的周围,还分布着不断聚合离散的人:贪婪的餐馆女老板锱铢必较丑态毕露;流塑料花姐倏然出场又遽然离世;车行伙计小发又热情又世故;社区服务站的厨师阿甘很有爱也很油滑;女同事小月与他情愫暗生又离港返乡;阿旭父亲做人尴尬处境难堪……所有的情景都如同一面镜子,照出香港社会的世态炎凉。而《幸运是我》更有一种意识流小说般的高妙,常常在最具戏剧冲突之处,反其道而行,镜头一转,营造出别具一格的人生真实。
比如阿旭缺钱,发现芬姨脑子不好使,就卖掉了她家的两把古董椅,买回一台3D电视机,果然芬姨只抱怨遥控器找不到亚洲电视台,一直未察觉古董椅没了,直到后来两人争吵时阿旭主动说出此事。此时影片的处理非常克制:芬姨有失控,阿旭有抱歉,但是重点不在古董椅价值,而是芬姨恍惚不定的记忆,阿尔茨海默病才是他们要共同应对的困境。性情不羁的阿旭,心地善良温厚,看到芬姨的老年痴呆状态,让他意识到责任,她需要他的照顾。
及至阿旭被父亲公开抛弃,芬姨要收留阿旭,那办法既天长地久又无比现实,她拉着他去律师事务所立下遗嘱:身后房产归阿旭,生前他要给她当儿子。突闻此事,阿旭茫然无措,接下来两人转回家,阿旭帮芬姨染着头发问:“为什么这么帮我?”芬姨说:“做人就是你帮下我,我帮下你。”
不断染霜的发色,是芬姨的重要生活内容,电影开场芬姨一出镜,就是揽镜自照检视白发;中间阿旭离开她家,她顶着一头墨鱼蛋式的染发膏,满大街乱走寻阿旭;现在,终于有他为她对付这些鬓角华发了,换言之,她有他来一起对付未来光景了。
这时阿旭也被获准去了解芬姨的昔日光阴。她原系名噪一时的红歌星,还能画电影海报谋生,爱过一个叫查理的乐手,后来那乐手出海淹死了,所以陪阿旭去祭拜母亲时,芬姨说自己死后骨灰洒进大海,她要与查理在一起。这个场景充满喻意,芬姨既实现了阿旭母亲的身份转换,又确定了自身归宿。在整部影片中,两人外出总是阿旭走在前芬姨跟在后,拉开十几米的距离,从芬姨母亲灵园出来,阿旭停下脚步转身伸出手,仿佛母子同心的一个仪式:这里比较滑,我们一起走吧。
被父所弃的阿旭遇到芬姨,孑然一身的芬姨收留阿旭,一个是年轻游民得到寄身之所,一个是晚境暮年有了终老之处,至此,不可根治的阿尔茨海默病,不再是个体生命的绝症,而是他们命运的一部分,被他们两代人共同承担起来,《幸运是我》片名中的“我”,既是芬姨,也是阿旭。或许,对于能偶尔看到这影片的观众,也未尝不是一种幸运。
同样的题材,前些年有一部《我们俩》,影片里的老北京独居老妪和外省女学生,也是从磕磕绊绊的生活细节展开,磨合掉各自性情里的不和谐处,培养出跨逾血缘的亲情,终至生离死别的深情相忆,房东老太太和租客小姑娘之间情绪与情感的起承转合,用的多是线条冷峻的勾勒,很多场景是北方的冬天,镜头多是灰灰的冷调子,貌似纪录片风格,骨子还是努力令人动容动情的小清新文艺片追求。
相比之下,《幸运是我》则汇集香港本土电影的生态百相,影片的氛围与情节仿佛《桃姐》和《天水围的日日夜夜》的交集之作,它有《桃姐》式的母子温情,有《天水围的日日夜夜》式的世态描述。
《幸运是我》是香港导演罗耀辉的处女执导之作,典型的小成本制作,罗耀辉曾做编剧多年,此次拿自己关注多年的阿尔茨海默病的社会话题入手自编自导,是要尝试一番自由风格的新导演手法。近年来的香港导演多有年轻面孔令人瞩目,香港政府给青年电影人的不仅有形而下的扶持,还有形而上的要求,有青年导演与前辈许鞍华交流的结果是:“不是给年轻人一部机器就能拍出电影,要看有没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照此标准看,香港本土电影的后续之才与复苏气象,已然VV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