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涵式”转型:地方本科高校发展的正途
时间:2022-08-06 08:05: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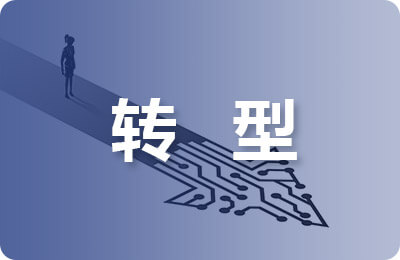
摘 要 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要从根本上转变办学指导思想和人才培养模式,避免“外延式”形式化做法,走“内涵式转型”的正途。国际经验表明,应用技术人才是高校、行业企业、社会组织等多个主体协同培养的结果,仅靠地方本科高校自身努力难以实现“内涵式转型”。产教融合、多方协同是新型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方式的运行要旨。必须树立“人才培养链条化”思维,明确企业主体责任,强化行业协会作用,构建校企结合制度性平台,以此推进地方本科高校实现“内涵式转型”。
关键词 内涵式转型;地方本科高校;人才培养链条化
中图分类号 G6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5)36-0028-04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指出,为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将“以举办本科职业教育为重点,融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于一体”。由此可见,部分地方本科高校转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后,办学类型将发生根本转变,不再以普通高等教育为主,而以举办“本科职业教育”为重点;将以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为主要目标,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主要路径。此举势必要求地方本科高校在办学指导思想、人才培养理念、治理结构及运作模式等方面进行由表及里的根本转变,进而在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育教学管理的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实质意义上的根本转变,是为“内涵式转型”。反之,如果体制机制不变,运作模式不变,仅在理论型的外衣之下搭些应用型的配饰,仍是“研究导向”“理论为主”,以闭门造车的方式培养人才,即使增加了应用型专业或应用型课程,仍然不能培养出应用技术人才,是谓“外延式转型”。实践表明,“内涵式转型”才是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本义和正途。
一、内涵式转型之因:改善应用技术人才供需现状的迫切要求
国家推动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初衷,是为了适应技术进步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的发展需要,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造更大人才红利。地方本科高校实现转型发展,核心是要解决两大关键问题:一是策应地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社会发展需要,调整专业结构、优化专业布局。二是顺应行业企业对人才类型、规格的实际需求,转变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前者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校人才培养在数量上的要求,目标是总量平衡、结构一致;后者关乎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要求在人才供需之间实现类型一致、规格相符。两者之中,哪个更加迫切?根据河北省社科院的近两年《河北人才发展报告》,以及笔者对部分企业所做的实地调研,我国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焦点在于人才“类型”而非“数量”,具体表现为:
第一,本科毕业生总量供过于求,企业紧缺人才却存在大量缺口。根据调查统计,2013年,河北省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含新能源),紧缺人才总数为93312名,其中本科人才紧缺25132名。在紧缺本科人才中,管理类本科人才紧缺8455名,科技类本科人才紧缺6388名,技能类本科人才紧缺10289名。与此同时,该年度全省各普通高校相关专业(统计范围为工学、理学、管理学三大学科相关专业)本科毕业生总数为87626人,远远高于25132人的需求总数[1]。
第二,“从业经验”超越“学历层次”,成为企业招聘人才的首选。调研发现,河北省战略新兴产业对紧缺人才的从业经验要求很高:2013年紧缺的93312名人才中,5年以上从业经验的需求人数为21094名,3~5年从业经验的需求人数为19303名,2~3年从业经验的需求人数为24384名,而对2年以下从业经验的需求人数为28531名,仅占总量的30.5%,其中对本科层次2年以下从业经验的人才需求数量更少[2]。
以河北省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中的部分典型企业为例:中钢集团邢台机械轧辊有限公司2012年5581名员工中,有博士2名,硕士72名,本科596名,专科1330名,高中及以下人员3581名,本科学历员工仅占10.6%。分类别来看,科技类人员440名,其中本科学历260名,大专及以下121名;技能类人员4353名,其中本科学历52名,大专及以下学历4301名。在新能源产业方面,作为全球最大太阳能单晶硅生产企业的晶龙集团,2012年共有员工1715名,其中含博士5名,硕士6名,本科280名,专科1121名,高中及以下人员303名,本科学历员工占16.3%。分类别来看,科技类人员800名,其中本科学历140名,大专及以下659名;技能类人员565名,其中本科学历50名,大专及以下学历515名[3]。
产业的紧缺人才为什么主要是有多年从业经验的人员?一个合乎逻辑的可能解释是应届本科生的“类型”不符合要求,“应用”优势不明显,在职业素养和实际能力方面准备不足,毕业之际处于“半成品”状态,至少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较好适应工作要求。由此可见,相对于社会实际需求,高校毕业生不是总量不足,而是类型不对;不是学历层次不够,而是培养规格不符。社会需要的是高素质应用技术型人才,而高校提供的是类型规格模糊的半成品。由于我国普通高等本科专业目录的制定权限集中在教育部,“基本专业”名称全国统一,“特设专业”的设置条件严苛,专业核心课程整齐划一,现有专业目录和培养规模足以在量上达到社会需求,因而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重心在于彻底扭转人才培养模式,走“内涵式转型”之路,才能真正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应用技术人才。
二、内涵式转型之路:高校难以“独肩担道义”
仅靠地方本科高校自身努力,就能实现“内涵式转型”吗?在应用技术人才的培养方面,政、产、学、企各自应有什么样的担当?换句话说,应用技术人才的培养体系是以高校为中心的“圈层式结构”还是政、产、学、研、用各尽其能的“链条式结构”?欧美国家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体制及运作机制,对我国地方本科高校实现“内涵式转型”具有诸多启示。
第一,政府主持、产学深度融合的人才培养体制。产学结合由学校力推还是双方依靠市场调节机制“顺其自然”?澳大利亚的经验是政府全程介入,积极搭建平台,做全职红娘:从测度社会需求到设置相应专业,从课程开发到教材编写,都由政府职能部门或委托专业机构主持,从而保证行业深度参与、产学深度融合。相关部门和机构包括:一是“行业培训咨询委员会”,专责人才需求的考察调研、分析整理,报经州教育培训部(DET)批准后,再由TAFE学院以及其他类型培训机构申请设置相关专业、确定招生数量,以避免在专业设置上供需脱节、重复闲置。二是“行业技能委员会”,由政府聘请的行业权威、企业人员为主、包含教育专家在内的多方代表组成,广泛调研、定期访谈相关企业,动态跟踪行业前沿,掌握人才需求的类型和规格,主持制定技能标准,以此作为制定“培训包”和确立教学内容的依据。三是“州教育服务处”。该机构由行业的人员为主组成,各州根据行业类别的不同可以对应设立多个教育服务处,专门进行课程开发,将课程统一编号、统一学时、编制提供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学指导资料,然后交由TAFE学院组织实施[4]。
第二,校企全面协同、行业全程参与的人才培养平台。人才培养应当是高校“独肩担道义”还是校企“合力分担”?德国“双元制”的启发是:高校和企业是人才培养同一过程两个互相借重的单元。在德国,企业全程主动参与人才培养,校企双方在同一人才培养框架下,制定相互衔接的培养计划,共享资源,共组团队,阶段交替培养学生,呈现“双中心”形态,企业成为学生完成技能训练、培养应用能力的重要中心[5]。在澳大利亚,占全国高校55%的应用型大学,高度重视且普遍推行“基于行业的学习”(Industry-Based Learning /IBL),企业全方位、实质性参与人才培养过程,学生轮换完成在大学的课程学习与在企业的工作实践。在IBL期间,学生由企业主管、学术导师和 IBL协调员三方进行管理和指导,针对实际问题展开专业训练,真实体会职场环境,能够较早培养更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学校与企业之间在人才培养上实现了全面融合[6]。
第三,教师有力支撑、全程应用导向的人才培养方式。培养应用型人才,先要有应用型师资;在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全程坚持应用导向。在德国,教师实行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参与项目驱动式的学习,在毕业设计环节选取行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实行“真题真做”。在澳大利亚,政府通过制定实施相关法律法规,确保职业教育机构和应用型大学教师具备行业经验或随时掌握行业发展状况。例如TAFE学院的专任教师,一般在大学毕业后要有5年行业经验才能入职;获得教职后,每年仍需在相关行业至少工作10个工作日(或连续工作,或每周工作若干小时;或有偿兼职,或志愿奉献);无论教龄多长,为保证教师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能够跟上产业要求,教师每隔3年都要参加一次执教资格培训并通过相关证书考试。在师资构成上,包括终身教师(Permanent Teacher)和非终身教师(Non-permanent Teacher),前者又分为全职和兼职两种,后者包括合同制教师(contract)和临时教师(causal),这四类教师所占的比例大约为40%、15%、30%、15%。由此可见,来自行业的兼任教师占有很大比例,由此确保教学培训内容紧跟行业实际。在教学方法上,澳大利亚教师非常重视“问题导向”,经常设计以模拟解决行业实际问题为内容的系列练习,并以提供综合解决方案为目标将其打包布置,称为“作业包”(Portfolio Work),期末成绩往往只占总成绩的很小一部分。
从国际经验来看,应用技术人才是高校、政府、行业企业、社会组织等多个主体,通过多环节、多层面、灵活、开放的协同而培养出来的。如果囿于地方本科高校内部谈论专业设置、师资队伍、教材建设、教育教学方式等问题,不去深思微观问题背后更深层面的体制机制问题,不综合思考人才培养的主体构成、动力机制和实现路径等问题,视高校为人才培养的核心甚至唯一主体,则很难实现“内涵式转型”。
三、内涵式转型之困:需要政府“挺身而出”
加快推进地方本科高校“内涵式转型”,大学、政府、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无可回避。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建设“应用型大学”的探索,倡导“产学合作”“工学结合”“产学研联盟”“政(官)产学研结合”“产学研用结合”,等等,有过很多尝试但效果差强人意,存在诸多体制机制障碍。实践证明,在我国特有的办学体制下,单靠学校在细枝末节上修修补补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政府必须肩负充分的主体责任,为地方本科高校实现内涵式转型纾忧解困。
第一,加快建立统一协调的政府管理体系,自上而下理顺人才培养体制。国外成功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莫不起自良好的顶层设计,以协调、高效的政府管理体制为依托,自上而下顺畅实现了产学融合、学用一致。反观我国,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呈现“自下而上”的倒推态势:首先起自教师层面探索“学生参与、问题导向、精简理论、强化实践”的教学改革,学校层面则竭力加强校企联系、完善人才培养方案,但在政府管理体制方面,依然是九龙治水、分割散乱的状态。例如行业人才需求预测和人才培养管理的职能,分属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两个部门互不隶属,有些下属机构职能密切关联但互不沟通,造成管理分散、协调困难,难以在产学之间形成深度融合的顺畅机制。只有率先解决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主体上的本末倒置问题,才能打开产学融合上蓄势已久的闸门。
第二,强化行业协会作用,校企共建应用型人才培养平台。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内在需要行业的全程参与。目前在专业设置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方面,各地高校基本采取“学校主导、院系主持、教学管理人员具体完成”的组织模式,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闭门造车的问题,但未能从根本上扭转高校自说自话的弊端。高校一心推动“校企结合”,却没有组织协调企业参与的权威和能力;企业渴盼适用对路的高素质人才,却没有投身人才培养实际过程的内在积极性。造成这种怪象的体制机制根源之一,是作为政产、校企中介的行业组织长期发育不良、功能缺失和先天性肌无力。借鉴澳洲“行业技能委员会”和“行业培训咨询委员会”的做法,我国应大力发展行业协会或类似组织,强化其行业技能标准认定与行业需求调研职能,将行业组织由行业自治性质扩展升华为既为行业出力、又谋人才公益的“准公共组织”,成为促进校企结合的制度性平台。
第三,加快构建“双师型”教师队伍,率先推动新建本科院校实现转型发展。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最终要依靠教师落实,从实地调研情况来看,应用型教师队伍建设存在诸多障碍:评价地方高校师资队伍的主要指标仍是高学历高职称教师比例、学术带头人数量,而非高素质应用型教师状况;改善教师队伍的主要倾向措施仍是引进博士硕士或鼓励教师到名校进修,而非将校企结合、深入行业一线作为发展要务;教师年度考评首重学术成果,职称晋升一律看齐学术水平。要想顺畅实现地方本科高校内涵式转型,政府可以推动新建本科高校先试先行,在新建本科高校教师招聘和职称评定上实行分类管理,避免“学术导向”一刀切;鼓励新建本科高校教师愿意而且能够深入行业企业或其他用人单位,以问题为导向,教、用相通,学、用一致;吸引行业一线人员到高校兼职,用其所长、提供便利;推动产教深度融合,依靠真切的利益连带激活人才培养链条。
参 考 文 献
[1][2][3]河北省社科院.2013年河北人才发展报告[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4:32-33.
[4]冯梅.澳大利亚TAFE学院校企合作实践的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1:33-39.
[5]张宁新.“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的本土化探索与实践[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2):16-18.
[6]陶秋燕.澳大利亚应用型大学的课程体系及办学特征分析[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6(9):23-26.
Abstract The local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should follow a right way in the current course of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which means changing its guiding ideology and talents training mode fundamentally, pursue “connot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avoid “extensive transformati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shows that it’s a collaborative result for the universities, industries, enterprises and other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foster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so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local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to realize “connotative transformation” with its own efforts. The key points of the new education and talents training mode include “fusion of university and industries” and “multilateral synergic cultivation”. The local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should set up a “talent training chain” thinking, so as to clear the enterprise’s responsibility and strengthen the industry association’s function, which will combine the universities with enterprises through institutional platform and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nnotative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connotative transformation; local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talent training chains
Author Zhao Jianbin, professor and vice principal of Xingtai College(Xingtai 054001); Ma Qingdong, professor of Xingtai College; Huang Yanping, Xingtai Colle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