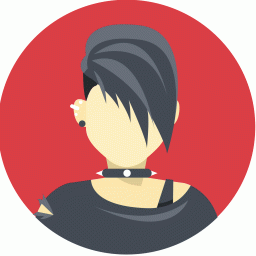保护语言保护我们的家园
时间:2022-07-28 05:43:11

太多的人都多次的论述过乔治・奥威尔(1903-1950)创作于1948年的小说《一九八四》。大家都看到了小说中的政治色彩――反极权与呼唤人性。公认这是一部“反乌托邦”的政治寓言和讽刺小说,反映了极权统治对人个性的压制,充满了对人类未来的担忧和绝望。
奥威尔的写作十分政治化(他的大多数小说都是最好的注脚),对这一点奥威尔本人并不加掩饰,然而,仅仅看到其政治姿态,无疑仍是解读过程的损失。极权不过是种人类压力的外在赋形,它既是极权本身又超越极权界限,因此本文更愿意把这本书看成是一本讨论哲学的书,有关于语言、权力与记忆的问题。奥威尔在这里冷峻地指出权力与语言如何勾结致使人丧失了领地――丢失了记忆与未来。
让我们从小说本身谈起。这部作品描述了想象中的“未来”――1984年的世界景象。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三国为了维持国内的和平而相互之间持续发动战争。小说以大洋国的角度展开。该国由“老大哥”统治,其势力无所不在却无影无踪。人们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小说主角是温斯顿,这是“最后一个人”。他一直在潜意识里抗拒InnerParty(Party),如同唐・吉诃德,而他的理想在现实面前彻底被击败,并且也像唐・吉诃德一样临终时真诚的反思,他心甘情愿的否定了自己,由衷地爱上了InnerParty(Party),失却了独立判断和对鲜活生命的回忆。这就是奥威尔所写的最后一个人的命运。
在《一九八四》中,InnerParty(Party)和老大哥所建立的巨大而且不可战胜的权力体系和传统的政治权力体系并不一样,它是和语言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即不仅仅将语言作为工具,而是将其视为权力本身。这正是20世纪语言观的一个转变,从而使奥威尔具有了很多现代性。罗兰・巴特说权力“无处不在永久延存的原因是权力是一种超社会有机体的寄生物,它和人类的整个历史,而不止是和政治的和历史学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在人类长存的历史中,权力寄寓于其中的东西就是语言,或者再准确些说是语言必不可少的部分:语言结构”。而对语言与权力关系论述最为权威的福柯不无忧伤地宣布他的结论:“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和语言的世界。”也就是说人类历史文化只是某种话语的构造,那么为什么人们这样说而不是那样说,福柯揭示说那是因为背后的权力关系。《一九八四》中Innerparty通过权力使真理本身更加暧昧不明。因此2+2=3,2+2=4,2+2=5,均可成为正确的等式,而“我们”既然没有话语权,即使最为浅显的东西如果失去了表达都是不能存在的。通过控制话语权可以控制知识、控制真理、控制现在,它说大洋国一直在和某国打仗就是一直在打哪怕昨天还和它是同盟。
但是,如果时间是河,生命是流,过去总会不知不觉向现在和未来渗透,传递信号,甚至有一天会颠覆未来,因此最重要的是控制记忆。正如那个宣言:“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控制过去的关键在于对记忆的训练,也就是一次次的篡改过去。“篡改过去是英社的中心原则。这一原则认为,过去并不客观存在,它只存在于文字记录和人的记忆中。”那么要控制过去首先就是控制语言(记录)。
真理部是控制语言和过去的重要机构,温斯顿是真理部记录司的工作人员,他的工作就是根据当前的政治形式对过去的一切记录(书籍、报刊、电影、录音、图画、照片等等)进行修正,使之符合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凡是与当前需要不符的任何新闻和任何意见,都不许保留在记录上。“全部历史都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在不断的修正中,正如InnerParty的原则所认定的,并没有什么是客观,什么是真实,历史已经停止。因此办公楼里有许多装置专门处理废纸用,称为“记忆洞”,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味的称谓。――消灭记忆,方法便是消除记录,人的记忆因为记录被“黑洞”吞噬而丧失了,这样过去不止是被篡改了,它其实是被消灭了,当除了自己的记忆没有任何档案存在的时候,个体又怎么能确定一件事情;而没有可供参照的标准,我们只能接受历史的虚构。即使还活着的人也没有能力对一个时代进行总结,正如小说中提到的那些经历过历史的老人,他们都无法言说到底现在的时代和过去的时代有什么区别,是否和InnerParty说的一样,可见我们依赖的只是叙述。
对于温斯顿在记录司的工作,奥威尔详细地描写了他的一件任务:改变老大哥的一次发言,因为在这次发言中提到了一个现在已经“化为乌有”的人,为了彻底抹去这个人曾经存在过的印记,温斯顿最后完全改变了这次讲话的内容,他即兴编造了一段关于一个“奥吉维同志”的事迹,把他塑造成为一个完全符合要求的人物,最近刚刚在作战中英勇牺牲,奥威尔写道:“奥吉维同志在现实中从未存在过,如今却在过去存在,一旦伪造工作被遗忘后他就会像查理大帝和恺撒大帝一样真实的存在,而且也有同样的证据可以证明他的存在。”查理大帝和恺撒大帝存在的真实性来源于历史对他们的记录,而在温斯顿完成改写以后,在新的历史中奥维吉的存在具有了同样的真实性。语言不仅具有表达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具有建构生活事实的力量,因此控制了语言也就意味着控制了思想,进而控制了对社会现实的建构。这便是奥威尔的语言和权力和记忆的观点。
正是出于以上对权力、语言、记忆关系的深刻认识,大洋国在传统英语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被称为新话(newspeak)。“新话的目的不仅是为英社拥护者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的手段,而且也是为了使得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再存在。”但是传统语言不能马上消失,这就依赖权力对语言施加暴力。正如福柯所揭示的“话语现在不是自生自灭的,它受到社会程序的制约,而这些程序中最为人知的是排斥程序(exclusion),排斥最主要的表现方式是禁止(prohibition)。禁止这一程序十分显著,也就是说,有一些话语是被允许出现的,而另一些话语则是不让出现的。人们并不能随心所欲的谈论什么:有些对象被禁止谈论,有些仪式被禁止谈论,有些特征主体也被禁止谈论。”而书中的现实也正是这样的,从而导致新话词汇大量减少,缩小词汇即是缩小思想的范围。“到最后我们将会使思想罪变得不可能再犯了,原因仅仅在于它们无以名之,因此也是不可想象的。”正如其中一个制造新话最后也被“蒸发”掉的的工作人员塞姆说的“话语控制思想”。语言的名与实已经打了很久的官司,但掌握话语权的人掌握天下已成颠扑不破的真理。
然而人的本性不是束手待毙,正如柏拉图所写人的灵魂有种向上飞升的前世记忆,因此作为最后一个人的温斯顿也试图做了很多斗争,希望有些东西可以存留在他的大脑里,以此作为抗争的秘密武器。他首先依赖的还是语言。文字虽然整体上被控制了,但总有某些角落里还有残留,不错,温斯顿曾经不经意发现了留有过去记录的一小片报纸,――毕竟这是文字,我们可以信赖,“这一件是实实在在的证据,是被消灭了的过去的一个碎片,就像在某个地层里出现了一块不该出现的骨头化石,因此打破了某个地质学理论……”然而这件保护回忆、对抗权力的物件并没有带给我们希望,奥布兰审问温斯顿时指出他曾看到的那片报纸,“成灰了,甚至辨认不出纸的痕迹,是尘土。它不存在,从来没有存在过。”“但是它存在的!它是存在的,它在记忆里存在着”“在记忆里,说得很好,但是我们,控制着所有的档案,我们也控制着所有的记忆,因此我们控制着过去。”权力无处不在,而在权力和语言勾结之处并没有自由判断,连无意识也不是自由的。所以温斯顿最后彻底忘记了那一小片报纸,他不相信甚至都不再去想到它了,他的记忆因此消失,并自动成为权力的同谋。奥布兰曾经对温斯顿说:“如果你是个人你就是最后一个人”。
在过去我们对记忆总是怀有某种乌托邦式的寄托,认为记忆有可能不需要文字――它难以磨灭,总是寄居在或许最不经意的地方,然后沉睡,而在某种不经意中又被唤醒,从而人可以战胜时间,获得某种哲学意义上的长存,这也就是普鲁斯特的哲学,这就是他在15卷小说里反复细致入微的描述的“非意愿记忆”,他以为这更持久更个人化也更有生命的本真,“假若没有记忆助我一臂之力,我独自万万不能从冥冥中脱身”。温斯顿的斗争最重要的方式也是普鲁斯特式的,所以他常因为咖啡的气味,巧克力在唇齿间的融化还有至纯葡萄酒淡淡的苦,而把那个以为是虚幻的过去拉近。小说中还写到温斯顿的一块小小的镇纸,一块美丽的过时的镇纸,里面有块小小的珊瑚,这是小说里凄美的道具,当茱莉亚(温斯顿的恋人)问道:“你觉得它是作什么的?”“我觉得它什么也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它没派过什么用场,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原因,它是他们忘了篡改的一块历史,是来自于100年前的一则信息,如果你知道怎样读的话。”似乎奥威尔在暗示我们保护记忆的某种方法。但结局呢?他并没有如普鲁斯特一样复活过去――镇纸被摔碎了;他被洗脑了,如一具活尸,真诚的爱着本职工作,等待着死亡,连当时的那些怀疑也一并埋葬了。普鲁斯特与奥威尔相比,普鲁斯特更温良、烂漫、纤弱,他像个贵族,文字是他的徽标,记忆是他的手杖,能够在小玛德兰点心里复活一切意愿与氛围。但奥威尔掐灭这豆希望之火,更残忍地指出,对于一个民族,对于大众,这些不经意的残留又是多么微弱和经不起考证,我们的记忆我们的历史只能由语言承载,一切仅在语言中,如果失去了文字,就是丧失了身份的确定性。或许对于整个民族的记忆来讲,奥威尔也发现了真理。语言和权力互为寄生,控制了思想和记忆,这是昆德拉所言的“有组织的遗忘”,后果是可怕的,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过去不再有意识,自我就会渐渐消失。
假若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所描述的世界真的出现,我们的语言被剥夺,那个时候我们靠什么来回忆?普鲁斯特式的挣扎,非意愿记忆也丧失了战斗力,因为它也是靠语言的自由才得以存在的,一切感觉都需要语言为之赋形。然而温斯顿是最后一个人。或许这正是该小说反乌托邦性的最好体现。失去了羽翼只能降落为尘。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思的人们与创作的人们是这个家的看家人”。因此保护语言,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